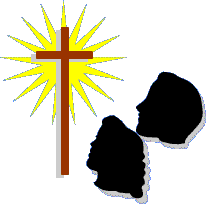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出现了两位光芒四射的思想家,一位倡议宇宙间有造物主,一位彻底反对;前者是鲁益师,后者系弗罗伊德。他们未曾谋面或直接论辩过。 哈佛大学副教授尼可里,二十五年来钻研两位的论著及私人信函;且在哈佛开课,比较两位的世界观,将心得整理成书:The Question of God。本专栏刊登书中各章菁华。 人生在世,谁都难逃身体或心灵上的痛苦,说它是生存中既定的一部份一点也不为过。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们便不时制造并承受各种形式的痛苦,许多人更是在痛苦中死去。 对弗罗伊德,以及信主前和初信时期的鲁益师而言,要接受宗教世界观的最大障碍在于:上帝充满大爱的仁慈形象与人所承受的痛苦实在太不协调。弗罗伊德和鲁益师都曾问道:“如果神真是至高无上的宇宙主宰,如果祂真的爱我,那么祂怎能坐视我承受这一切的痛苦?可见祂不是子虚乌有,就是毫无实权,再不,祂根本就不在乎人间的疾苦”。最后,佛氏下的结论是,世上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但鲁益师却有不同的看法。 弗罗伊德三岁时,深爱的保姆因故离去,晚年时亲人相继离世,其中包括他最钟爱的一个女儿及孙子。失亲之痛使得佛氏一生都在忧郁的笼罩下度过。 然而,没有什么比在维也纳延烧的反犹太热潮更令弗罗伊德苦恼的了,他就读维也纳大学时感受尤深。他在《梦的解析》中写到自己的小学阶段时说:“我第一次体会到,被视为异类意味着什么。其它男孩子的反犹太意识提醒我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当父亲告诉他,自己在人行道上受人凌辱,却又隐忍屈从的一段故事时,他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 弗罗伊德回忆,“我当时觉得,这些反犹太举动实在是以大欺小,就像孔武有力的大男人拎起一个小男孩一样”。当年伟大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Hannibal)曾向父亲发誓,要向罗马讨回公道,“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汉尼拔象征着犹太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而罗马则代表天主教的势力”。当时绝大多数的维也纳人信奉天主教,因此弗罗伊德将天主教与反犹太主义划上等号,也从此埋下一生与天主教为敌的种子。 弗罗伊德十七岁时进入维也纳大学,直到数十年后,他仍清楚记得在大学里所受的排挤。起初,他面对反犹太主义时的表现并不如汉尼拔一般的英勇,但他坚忍不拔的毅力却颇有这位将军的气势,“大学时代的恶劣感受……使我很早就熟悉,身为弱势团体遭‘主流团体’排挤的宿命,也奠定了日后独立思考的基础”。 成年后的弗罗伊德一直认为,反犹太浪潮是导致他的精神分析学四处碰壁的最主要原因。佛氏在给同事的信中明白地表示,他的学说备受攻击是因为反犹太意识作祟:“我们犹太人若想成为团体中的一份子,一定得具备一点受虐的精神,承担别人不公平的对待,否则很难与其它人打成一片。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的姓是Oberhuber(译注:德国姓氏),那么我所提的新观点无论如何也不会遭遇这么多的反对声浪”。 弗罗伊德在防堵精神分析学被视为犹太科学的道路上,遭遇了重重困难,1912年时,他已表达了不耐:“令我烦忧的是,当我试着联合犹太人、亚利安人或反犹太族群共同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而努力时,他们最终还是再度像油和水一样地分开”。 来自德国医界及科学界的围剿及嘲讽让弗罗伊德极为失望。虽然他勇敢地克服心中那份沮丧,继续扮演“众矢之的”的角色,但来自外界的排挤却使他一生受苦。弗罗伊德在将近八十岁那年写道:“……以他们的自大,对逻辑无理的藐视,以及粗鲁又没格调的批判而论,我认为任何说词都无法替他们辩解……伤我非常之深”。 在〈一个五岁男童的恐惧症分析〉(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这篇论文中,佛氏针对反犹太思维提出了精神分析学上的诠释:“阉割恐惧(Castration Complex)是人们潜意识中反犹太主义最根本的源头;因为就连托儿所里的小男孩都知道,犹太人的阴茎上有一个部份遭到割除--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器官是不完整的--这给了他们歧视犹太人的权利。男人潜意识中自认比女人优越的最主要原因也在此”。 弗罗伊德在最后几年所写的《摩西与一神论》(Moses and Monotheism)中,归纳出反犹太主义的三项“深度动机”:第一,人们嫉妒犹太人是上帝拣选的子民。“我敢大胆地说,即使到今日,人们对于自称是父神最钟爱的首生子民依然存有嫉妒心理--彷佛这项头衔有什么真实意义存在似的”。第二,就是先前提到的阉割恐惧。“在犹太人特有的传统中,割礼是项令人恐惧、憎厌的习俗,因为它唤起人们心中对阉割的惧怕”。第三反犹太意识实质上是一种对基督教的敌意--只是这股敌意后来转嫁到犹太人身上。“须记得今日那些最仇视犹太民族的人,是在历史后期才成为基督徒,而且还是迫于血腥高压统治的结果……他们对这个强加于人的新教仍带有怨恨,但却把这股怨气转移到基督教的根源上”。佛氏提醒他的读者,“福音书的故事围绕着犹太人打转使他们极容易成为人们憎恨的目标”。他总结说:“追根究底,这些人对犹太民族的憎恨其实就是对基督徒的憎恨”。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佛氏还举出纳粹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残暴行径为例。 弗罗伊德对纳粹的暴行有切身的体验。1980年六月,我造访了安娜·弗罗伊德,在佛氏家族服务超过半个世纪的女管家波拉,告诉了我一些可怕的遭遇。她提到黑衫军曾到家中来拘提安娜小姐进行侦讯,一行人离开前,弗罗伊德塞了一些氰化物的剧毒药丸给女儿,以防她遭受凌虐。 佛氏认为不只德国人或奥地利人对犹太民族有敌意。他在八十多岁逃到英国时,曾在信中提到他对英国人的看法:“一般而言,反犹太主义是种不外露的私密情绪,但我仍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当然,偶尔也会有例外的时候……就像世界各地一样,这里的反犹太情结无处不在”。 弗罗伊德在去世的十个月前,写信给曾引用他言论的英国《潮流》(Time and Tide)杂志的编辑:“难道你不认为这个讨论反犹太浪潮的专栏应该保留给那些非犹太族裔,立场比我超然的人来发言吗?”弗罗伊德认为,非犹太族裔应该重视这位编辑所观察到“国内反犹太意识日益高涨”的问题,并且挺身而出,遏止问题继续恶化。佛氏在这封信中概述了惨痛的亲身经历:“四岁的时候,全家就从一个叫做摩拉维亚的小镇搬到维也纳。经过七十八载的辛勤工作之后,却被迫离开家园,眼睁睁地看着一手建立起来的科学协会瓦解,相关机构毁于一旦,印刷厂……被入侵者占领。我的著作不是被没收,就是成了一团纸糊,连儿女都被工作的机构给开除”。 如果说反犹太主义是弗罗伊德所有痛苦的源头,未免言过其实。佛氏患有忧郁症、恐惧症(特别是对死亡),及身心症。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六年里,身体上还必须承受上颚癌所带来的痛苦。 1923年初,弗罗伊德六十七岁那年,他在口腔上颚发现了一块白斑。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他判定这是常在老烟枪嘴里出现的黏膜白斑病。弗罗伊德一天要抽上好几支雪茄,尼古丁已经严重成瘾。他知道这些病变组织可能转变为恶性肿瘤,但还是拖了几个月后才去请教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道奇(Dr. Felix Deutsch)。诊断的结果确为癌症。 第一次的手术并不顺利。当时佛氏选择了一位他认识的海耶医生(Dr.Marcus Hajek)来操刀,海耶医生在一家教学医院中设备简陋的门诊部替他动手术,过程中只用了局部麻醉。手术后,并发症旋即而至,开始大量出血。妻子和女儿安娜赶到时,发现弗罗伊德满身是血,坐在一张餐椅上。等到稳定下来,她们离开去吃午饭时,他又开始血流不止。由于无法开口,佛氏试着按铃求援,然而铃却正好坏了。这时房里的另一名病患,是位弱智的侏儒,发觉他的情况不妙,急忙找来救护人员,否则他可能性命难保。之后,安娜寸步不离地守在父亲身边。到了晚上,她发现父亲因为失血过多而显得相当虚弱,伤口也疼痛难耐。护士赶紧打电话通知驻院医生,但这位医生竟拒绝起床看诊。 多年后,弗罗伊德的一位医生写道,海耶医生“根本没有资格”进行这种复杂的手术。道奇医生最后将他转介到一位知名的口腔外科医师佩其乐(Dr. Hans Pichler)的手上。由于癌细胞相当顽强,他又替弗罗伊德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切除手术。 此后,佛氏进出手术房三十多次--每次都只采局部麻醉。由于口腔上壁被切除,医生改以一块替代金属片来分隔口腔与鼻腔,因此呼吸和进食变得异常困难。除此之外,多不胜数的X光检查及放射治疗所造成的后遗症,也为他人生最后的十六年带来极大的痛苦。 弗罗伊德变得不爱与人一同吃饭。有一次他和安娜在火车上,边进早餐边与一对初识的美国夫妇闲谈时,突然嘴里喷出鲜血,原来是面包的硬皮划开了先前的伤口。但佛氏仍不放弃假日出游,面对一切的折磨,也以淡然的态度接受。不过满腔的忿恨有时候也会爆发,就像他在写给友人费斯特的信中所说的:“请容我无礼一次!究竟你是怎么在遍尝人世的种种况味后,还能相信这世界有天理?!”佛氏自己下的结论则是,“人的命运受到某个冷酷无情、捉摸不定的恶势力所操弄”。 * * * * * * * * * * * * * * * * * 如果说反犹太运动造成弗罗伊德生命中最大的伤害,那么鲁益师幼年丧母,以及几十年后丧妻的打击,则带给他最漫长也最惨痛的折磨。将近半个世纪后,他仍能在自传中鲜明地的描述:“我和哥哥在母亲过世前就已感受到丧亲之痛。在吗啡的作用、母亲的精神失常及护士的奔忙中,我们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她,我俩的存在显得那么的突兀又多余”。 鲁氏回顾以往,才发觉原来孩童和成人对于伤痛有不同的感受,孩子往往会感到被孤立,与周遭的人有疏离感。他写道:“如果我的经验可靠,那么可以说,成人的哀伤和恐惧会使孩童产生惊吓和疏离感”。鲁益师及哥哥与父亲日渐疏远,也因此“越发相依为命……像两个受惊的孩子在凄风苦雨中,相互依偎取暖”。他回忆“被带到卧房中,见已去世的母亲一面”,看到母亲遗体时,“哀伤中满是恐惧”,以及带着惊恐“面对棺木、鲜花、灵车,以及丧礼等后事”。母亲的过世使得所有的快乐“都从生命中消失无踪”。 前几章曾提及鲁益师早年在寄宿学校的悲惨生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仅十九岁的鲁益师在前线亲历了战争的可怕,并且遭到夺走身旁同胞性命的炮弹炸伤。对于这段经历,他除了表示“多年来,大战的阴影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以外,并没有详加描述。 鲁氏从军期间得了“战壕热”,在前线的医院待了三个星期后再度回到战场时,正好赶上“德军大进攻”。“整个严冬里,疲乏和积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曾在行军间累到睡着,醒来时发现自己还在不断前进。壕沟里积水深及膝盖,穿着长达大腿的靴子走动时,偶尔会被隐藏的铁丝网刺穿,还记得冰冷的积水穿透靴子,涌进来的感觉”。鲁益师发现,虽然他常常在梦里见到战时的景象,但最骇人的几幕已逐渐模糊。他忆述:“那酷寒,那气味……那些血肉模糊的躯体,像被压扁的金龟子,仍在挣扎……遍地或坐或站的尸体;放眼望去寸草不生的沙场;日夜穿在脚上的靴子,彷佛已成为身上的一部份。这一切在记忆中渐渐模糊了起来”。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子弹呼啸而过的情形,当时心中的感觉“并不完全是……恐惧”,只是“耳畔响起一个细微的颤音--‘这就是荷马史诗里所形容的战争!’” 根据沙耶的说法,鲁益师在伦敦一家医院治疗伤口的期间,“心中异常寂寞,并且还患有严重的忧郁症”,有关战场的连连恶梦,使他难以入眠。现在看来,鲁氏当时是患了创伤后焦虑症。 后来,或许是因为世界观的不同,又或者是树大招风,牛津大学的文学院拒绝让鲁益师成为正式的教授,这对他而言又是一大打击。直到年过五十五,鲁氏才受到剑桥大学之邀,成为中古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的教授。不过最沉痛的打击,当然还是六十二岁那年失去了爱妻乔依。他一生中最害怕也最想逃避的,正是这种失去至爱的痛苦,却再一次经历了年幼时的恐惧。鲁益师或许极力想以童年时的老方法,来抑制自己的情绪。他试着用过人的才智来了解自己强烈的复杂感受,不让这些情绪操控他。他也试图透过书写,让所有的想法和感觉都跃然纸上,来剖析哀恸的整个复杂过程。鲁氏在《卿卿如晤》里写道:“我并不害怕,但那感觉就和害怕如出一辙,胃里一样地翻搅,一样地坐立难安,呵欠连连。我不停地咽口水”。 鲁益师表示,哀伤有时像喝醉了酒、或头部遭到重击的感觉:“……彷佛微微地醉酒或脑震荡”,这使得他自外于人群,很难与旁人产生互动。“外面的世界和我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布幔,我发现自己很难听进别人讲的话……觉得索然无味”。然而鲁氏并不喜欢独处,“希望能有人陪伴,我害怕屋里冷冷清清的感觉,最好身边的人彼此交谈,又不必找我说话”。 鲁氏为了减轻丧妻之痛,曾试着告诉自己要坚强,千万不能因此情绪失控。他安慰自己仍拥有许多所谓的“资源”,同时也提醒自己,婚前单身的日子也还算惬意。但他接着又写道:“一旦听从这样的声音,心中往往一阵羞愧,但也曾有那么短短的一刻,又觉得这么想不无道理。可是这时往日火辣辣的记忆随即浮现,彷若当头一棒,所有『理所当然的想法』立即有如炉口上的蚂蚁一般,消失无踪”。 鲁益师看到两个继子试图走出母丧的悲痛,也想起了自己童年时,面对母亲去世的反应。他发现:“我无法和两个孩子提到他们的母亲,一旦提起,两人的脸上就会浮现既非哀伤、也非关爱、又非恐惧或怜悯的表情,而是一种最隔绝情感交流的情绪--尴尬。他们看着我的样子,彷佛我正在做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恨不得我能赶快停止。而我在母亲过世后,每每父亲提起她时,也有和他们一样的反应。我不怪他们,男孩子就是如此”。 鲁氏对于必须透过书写的方式来审视自己的感受,也颇有质疑:“我不只每天活在哀伤中,而且是每天都意识到,自己每一天活在哀伤中。这些记录是否只会加深我的痛苦?只会让我的思绪不停地绕着同一个主题转动,单调地如同踩踏轮一般?”但他试图用唯一可能的说词来为自己辩解:“如果不这样,那我还能怎么办?我需要疗伤止痛的解药,而现在阅读对我而言,已逐渐失去作用。如果将所有的思绪全都写下来(所有的?不!不过是千丝万缕中的一小撮罢了),我相信多少能让自己跳脱这样的心境;至少我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 鲁益师担心,长此以往会使得他的情绪转为一种自怜:“……沈溺于自怜、咀嚼着那令人作呕的甜腻快感--自己都感到厌恶”。他不禁怀疑:“难道这些札记纯粹出于无法接受人只能默默承受痛苦的事实,而作的无谓挣扎?还有人相信,这世上有化解痛苦的方法吗?(但愿真的有!)这就像去看牙医一样,无论你是紧抓着椅子的把手不放,还是双手平摆在腿上,医生手中的钻牙器仍旧是不停地往下钻”。 在丧偶的悲恸中,特别感念妻子乔依带给他的亲密感,那是他婚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尽避婚姻中的两人明显地相异、对事情的看法也总是相左,但那种时时刻刻都能体会到的亲密感,却是婚姻带给我最珍贵的礼物--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真”。他呼唤着乔依:“亲爱的,亲爱的,回来吧!哪怕只是惊鸿一瞥!”失去了妻子,无异于失去了身体的一部份:“目前,我正学习拄着拐杖走动,也许不久后会装上义肢,但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用双脚走路了”。 他将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痛苦作了以下区分:“内心的悲恸,有如一架轰炸机在头顶盘旋,每绕一圈,就投下炸弹;肉体的疼痛,则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壕沟战,密集的炮火连续攻击数小时,没有片刻的歇息。思想永远不会静止;疼痛也常滞留不去”。痛苦的思想似乎永无止境:“还有多少回?难道就一直这样下去吗?无垠的虚空像一个庞然大物一再向我袭来,令我惊骇莫名,不禁感慨:‘直到此刻,我才恍然明白自己失落了什么’。同一只脚,一次又一次地惨遭截断,刀子刺进肉里的痛楚,一遍又一遍的啃噬着我”。 最后,鲁益师像许多在苦难中的人一样,发出了内心深处的吶喊--“神啊!你在哪里?”他说:“当你置身快乐之境,晕陶陶的,一点都不觉得需要神,甚至认为祂对你的要求真是煞风景;这时候,如果你清醒过来,向祂献上感恩、赞美,迎着你的--或是你觉得迎接你的--将是一双张开的臂膀”。但是当鲁益师最需要神的时候,祂却似乎消失了,“当你迫切地需要祂,当你孤立无援时,等待你的是什么?一扇在你面前砰然关闭的门,里面还传出连上两道门栓的声音。之后,便寂静无声。你最好还是掉头就走吧!等得越久,那片死寂越是令人不寒而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我们事事顺遂时,祂像个神气活现的指挥官;而当我们陷入困境时,祂却了无踪影?”一位友人提醒他,拿撒勒人耶稣在最需要帮助时也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二十七46)鲁益师回答:“难道这能帮助我解决心中的困惑吗?” 鲁益师不仅怀疑在他最迫切需要神时,根本无处寻祂的踪迹;而且经由诸多痛苦所传达出来的神的形象,也令他深感困惑。“我想,问题不在于我即将陷入不再相信有神的危险中;真正的危险在于我开始相信与神有关的一些骇人之事。我所惧怕的结论并非‘原来,神根本不存在!’而是‘原来,这才是神的真面目,别再自欺了’。” 鲁益师不断苦思:全能的神既然爱他,怎能容许他遭受苦难的折磨。后来,他领悟到,也许我们应该将神视为一个具有仁心仁术的外科医生:“祂越仁慈、负责,开刀时就越不徇情面。如果祂因为你苦苦哀求,而在手术还未完成前就停手,那么你先前受的苦不就枉费了?”但是鲁益师也怀疑这样的痛苦和折磨是否真有必要,他这样回答:“那么就自己抉择吧。苦难已临头,如果你认定那是多余的,则神不是虚幻不实,就是心狠手辣;如果你相信神是良善的,那么苦难就是必要的。若非必要,哪怕这位神只有些许的恻隐之心,也不会忍心将它加诸在人身上,或者根本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鲁益师问:“有些人说:‘我不怕神,因为祂是良善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都没看过牙医?” 鲁益师凡事追根究底的心态,使他心中起了一长串的疑问。在《影子大地》(Shadowlands)的舞台剧及电影剧本中也暗示,鲁氏对神失去了信心,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他的书信,以及许多认识他的人那儿证实,乔依过世后,他的信心比以往更坚定;至于他那些数不清的疑问,都只是针对神的形象。 鲁益师忆起新约中有个应许--叩门,门就会开,但是他发觉“只有深锁的大门、钢铁般的帘幕、一片空茫和凛冽的寒气”。鲁氏发现自己不仅止于叩门,他问:“叩门是不是指像疯子般地捶门或踢门?”最后他了解到,自己狂乱的呼救可能阻碍了神的拯救:“‘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毕竟,你必须要具备接受的能力,否则,即使是全能者也不能给你什么。也许,是冲动暂时破坏了你的接收能力”。 神的同在有如夏日黎明的曙光,渐渐鲜明起来,“当我转向神,迎着我的不再是紧闭的门;当我回头看H(鲁氏的妻子)时,也不再是空茫一片,她在我脑海中的一颦一笑,也不再困扰我。从札记中可以看出,自己已有些许进步,但与我所期望的还有一段差距。也许,因为没有突然的、惊人的和情绪性的转变,使这两种改变并不明显;就好像房间逐渐暖和起来,或是晨曦的照射,往往是在持续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引起你注意”。 鲁益师一连串的问题并未获得解答,但是却得到他所谓“极为特殊的‘无解’。不是紧拴的门,反而比较像是一种静默,但又绝非冷酷的凝视。祂并非拒绝我,只是好似对我摇头,把问题先搁置一旁,对我说:‘孩子,平静下来吧!这些事不是你能懂的’”。 鲁益师回顾那段哀痛的日子,领悟到自己之所以难有进展,是因为他的焦点是在自己,而非神的身上。他明白神“从未测试我的信心或爱,祂早知道这一切的本相,被蒙在鼓里的,是我”。也许透过亲身的经历,他才开始了解自己二十年前在《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中所说:“……痛苦的本身,说不上有什么好处,但对受苦的人和旁观者而言,痛苦的遭遇却有其益处--对前者,在于对神旨意的降服;对后者,则在于所引发的同情心与实际关怀。在这个堕落但部分蒙救赎的宇宙中,我们可以区分(一)从神而来单纯的善(the simple good),(二)叛逆的受造物所制造的单纯的恶(the simple evil),(三)神利用那种恶以达成救赎目的,以及因此而产生(四)复杂的善(the complex good)--由接受痛苦和为罪忏悔所促成的。虽然,神的恩典可以为人赎罪,但是祂能从单纯的恶制造出复杂的善这个事实,并不能作为行恶者脱罪的借口”。 * * * * * * * * * * * * * * * * * 最后,鲁益师摆脱了痛苦及信仰间纠缠的问题,然而弗罗伊德却不能。 弗罗伊德在《宗教经验》(A Religious Experience)那篇论文里直言,“神允许苦难发生”,因此神应该负责。他在给波士顿的普南博士写信时,也表达他的愤怒和蔑视:“我……对神没有丝毫的畏惧,假如有一天遇见祂,我要数落祂的不是之处,绝对比祂能数落我的还多”。受苦的人也许能了解佛氏的愤怒,但他既是无神论者,跟谁生气呢? 弗罗伊德的临床工作经验,使他了解痛苦的普遍性。根据他的观察,病人出现严重的情绪症状--甚至精神失常--往往是为了逃避现实中难以忍受的痛苦;当内在或外在的现实变得不堪承受时,病人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也许弗罗伊德为了解自身的痛苦,因而一直锲而不舍地努力辨识人类痛苦的主要来源。他在《幻象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中说:“大自然似乎借着许多灾难来嘲笑人类的控制能力:地震--撕裂大地,掩埋生命和文明的产物;洪水--四处泛滥,吞没一切;疾病--直到最近我们才了解那是其它生物对人类的攻击;死亡--人类医学至今对这令人痛苦的无解之题,仍然束手无策,将来也不可能找出对策”。 若干年后,他在《文明与其缺憾》中,又增加了一项痛苦来源,那就是其它的人类。“对我们而言,最后一项来源所带来的痛苦, 或许更甚于前者”。他总结道:“生命是难以承受的,很容易造成‘长期焦灼盼望的状态’”。 弗罗伊德以人世间的苦难来攻击“凡遵行神旨意的,必受祂祝福”这项论述。他说,举目四顾,好人和坏人一样逃不了苦难。他在《世界观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a Weltanschauung)中写道:“……宗教向来宣称,只要遵行某些道德规范,就能得到庇护和快乐……事实显示,这些承诺不值得信赖。看来宇宙中似乎并没有一位全能者,像父母般地呵护我们,为我们谋福祉,以求凡事圆满。……当地震、海啸、大火无情地吞噬生命时,其对象无分善人、恶人,更不分信徒或非信徒”。 弗罗伊德在谈到人际关系时表示,好人常处于劣势,“凶暴、狡诈、无情的人,往往坐拥世上令人羡慕的好东西;而虔诚的人却常是两袖清风。可见主宰人类命运的权势,是黑暗、冷酷又无情的”。佛氏认为,世人相信“宇宙的主宰”赏善罚恶的观念,“与事实并不相符”。 鲁益师则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现在“宇宙的主宰权”只是暂时落在仇敌手中。弗罗伊德对这种论述的回应与常人无异。他说,人因为无法将苦难和观念中慈爱的神融合在一起,于是凭想象捏造出一个邪魔来背黑锅。但他认为,就算真有魔鬼,神依旧无法推卸责任,毕竟邪魔也是神创造的,不是吗?鲁益师同意神创造魔鬼这个说法,但他不认为这就代表神是邪恶的,或神创造了邪恶。 鲁益师写道:“黑暗权势是神创造的,但它在被造之初是好的,后来误入歧途”。他在解释自由意志和邪恶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时又说:“神赋予受造物自由意志,也就是说,受造者可以选择行正路,也可以选择走偏路。有人认为,这世上可以有一种被造物,既拥有自由意志又不会误入歧途,我可没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假如受造物可以自由行善,当然也可以自由为恶,有自由意志,才有了恶的存在”。那么,当初神为什么要给人自由意志呢?他答道:“虽然邪恶可能因自由意志而生,但也唯有自由意志能使人拥有无价的爱、善和喜乐。一个机械化的世界--受造者全像机器般,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有什么被造的价值可言呢?” 然而,我们不禁纳闷:“难道神不知道,自由会导致种种邪恶和可怕的苦难?”鲁益师说:“神当然知道,人若误用这种自由会有什么结果,但祂显然认为值得一试”。 鲁益师还是个无神论者的时候,也和弗罗伊德一样地恼怒神。他写道:“我驳斥神的存在,因为这个世界看来既残忍又不公平。可是我怎么会有‘公平’或‘不公平’的概念呢?一个人除非先有直线的概念,否则不会说某条线是歪的……当我试图证明神不存在--换言之,整个现实都毫无意义--的过程中,却发现不得不假定现实中有一部份,也就是我对公平的概念,是完全有意义的。这样看来,无神论的理论架构未免太过单薄……”。鲁益师指出,新约的信仰“不是让我们用来解释苦难这种棘手现实的一套系统,苦难应该是用人的一套系统来加以解说。在某种意义上,信仰非但无法解决,反而是制造了痛苦的问题,若不是我们一面领受神是公义、慈爱的美好承诺,一面又要面对这世上种种的苦难,那么痛苦也就不成问题了”。 鲁益师说,痛苦是邪恶的。神没有制造痛苦,但祂可以将痛苦化为祝福。许多人是在遭遇痛苦或重大危险-例如,乘坐飞机遇到乱流时,才呼求神。他写道:“……痛苦绝不会让你漠视它的存在。神在我们享乐时耳语;在我们良知中发声;但在我们痛苦时呼喊--那是祂唤醒沈睡世界的扩音器”。然而,鲁氏警告,痛苦也可能使人远离神。“痛苦作为神的传声筒,是个可怕的工具;它可能导致人背叛神,永不回头”。他认为神可以利用痛苦帮助我们明白人需要祂,但有时候我们的反应不是转向祂,反而是背对祂。 弗罗伊德在面对生命中的痛苦时,采取的是他常提到的“认命”态度。他在《幻象的未来》一书中,描述了拒绝宗教世界观的人,其人生会呈现什么样貌;当中所说的,也许就是他亲身的体验。“他们必须承认自己全然无助……不再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也不再是慈爱的神悉心照顾的对象……面对命运中的重大困厄,将是孤立无援。他们只有学习以认命的态度忍耐种种艰苦”。 弗罗伊德在别人遭遇苦难时,常苦于“没有安慰的话”可说,只能劝人认命。当同事琼斯遭逢丧女之痛时, 他写信慰唁:“身为一个不信神的宿命论者,每当我面对死亡的狰狞,只能默默承受”。信中还提到孙子海涅利(Heinele)过世时,自己如何的痛不欲生:“我对人生已彻底厌倦”。佛氏似乎很明白,自己在遭逢逆境时,毫无可汲取的属灵资源。女儿苏菲离世后,他写信给一位同事:“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对一个非信徒而言,面对死亡,除了瘫软之外,没有来日的盼望可期……”。他想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也希望早日走到人生的尽头。 每个人都有痛苦,而面对痛苦的态度,则决定了它对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如果我们像鲁益师一样,相信有一位慈爱的至高者掌管我们的命运,那么,我们就能存着耐心和盼望来承受痛苦;但若抱持唯物主义的观点,那么只能照着弗罗伊德所言,向艰难的现实屈服。佛氏在总结时说:“如果信徒走到一个地步,发现自己最终不得不将一切归之于神那‘高深莫测的旨意’,那就等于承认:在痛苦中,无条件顺服是他最后的慰藉和快乐的泉源。如果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可能少绕许多弯路”。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