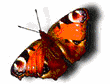|
本书声称,这并不是一本大事记,而是有关个人经历的记录,数以百万的囚徒反复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录。它是由一位幸存者讲述的、有关集中营的内幕故事。这个故事关注的不是已经得到经常描述的大恐怖〔尽管并不经常为人们所相信〕,而是数量众多的小折磨。换言之,它将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如何反映在普通囚徒的意识中? 这里所描述的多数事件并不发生于著名的大集中营中,而是发生于真正死去了多数人的小集中营中。这个故事既不讲述伟大的英雄、烈士的受难或死亡,也不讲述身名显赫的大头领—享有特权的囚徒—或众所周知的囚徒。它并不十分关注大人物的受难,而是关注众多不为人所知、没有记录在案的受害者的牺牲、磨难和死亡。它所讲述的正是这些普通的囚徒,他们的袖子上没有戴区别性的标志,常常为大头领所鄙视。当这些普通囚徒忍饥挨饿时,大头领却衣食无优;事实上,许多大头领在集中营的生活比其一生中任何时期都要幸福。他们对待囚徒常常比看守更凶恶,鞭打囚徒比党卫军更残忍。当然,集中营只从证明其性格适合于这一工作的囚徒中挑选大头领,而且,如果他们没有遵照执行他所应做的事情,他们将立即被免职。不久,他们就会变得与党卫军和看守十分相似。人们可以根据同样的心理基础来评价这些大头领。 对于集中营的生活,局外人很容易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一种混杂着同情和怜悯的观念。对于发生于囚徒中间的残酷的生存斗争,他们知之甚少。这是一场为了生计,为了生命,为了他自已,或者为了他的朋友而展开的无情的斗争。 首先让我们举一个转移的例子。有时,集中营当局会宣布将某一数量的囚徒转移到另一集中营;但是,较为可靠的推测是,转移的终点是毒气室。挑选的对象是不能干活的体弱多病者,他们将被送到配备着毒气室和焚烧炉的中心集中营去∶挑选的过程将意味着一场每个囚徒之间,或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为自由而展开的斗争。事关紧要的是,自己或朋友的名字能够从牺牲者的名单上勾去,尽管每个人都明白,每个人的获救将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牺牲。 每次转移都将会带走某一数量的囚徒。实际上,这井不算什么,因为每个人只是一个号码。在进人集中营付〔至少这是奥斯维辛的做法〕,囚徒的所有情况都由自己串报。因此,每个囚徒都有机会申报一个虚假的姓名或职业;并且,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当局只对囚徒的号码感兴趣。这些号码通常刺在他们的皮肤上,而且必须缝在裤子、茄克或上衣的某一部位。看守如果想要控告某一囚徒,他只需要漂一眼他的号码〔我们对于这一漂是多么地惧怕!〕;他们从不询问囚徒的名字。 人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欲望去考虑道德和伦理间题。每个人都为一种想法所控制:为正在家中等待自己归来的家庭而活着,并使朋友活着。因此,他将毫无犹豫地尽力安排另一个囚徒,另一个‘“号码”去替代他在转移名单中的位置。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挑选大头领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只有最残忍的囚徒才会被挑选从事这一工作〔尽管有些令人愉快的例外〕。但是,除了这一由党卫军操持的选择之外,在所有囚徒中还一直进行着某种形式的白我选择。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多年来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并在生存斗争中失去所有顾忌的囚徒才能存活下来;为了生存,他们准备运用任何手段,包括诚实的或不诚实的手段,甚至暴力、偷窃和出卖朋友。那些活下来的人得到了幸运的机会或奇迹的护佑——不管你称之为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中最优秀的人没有活下来。 许多有关集中营的事实早已记录在案。在这里,事实只有成为一个人的部分经历时才是重要的。正是这些经历的性质才是本文将要加以描述的。对于曾经作为某一集中营囚徒的人来说,本文将试图根据今天的知识来解释他们的过去经历。对于从未有过集中营生活体验的人来说,本文将有助于他们全面地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理解那些极少数的幸存者的经历,并进而认识到他们今天所处的艰难状况。那些曾经做过囚徒的人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经历。对于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所有的解释都是不需要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既不理解我们当时的感受,也不理解我们现在的感受。” 鉴于心理学要求保持某种程度的科学中立,提出一种解释这一主题的方法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当观察者本人就是囚徒时,这一中立还是必不可少的吗?旁观者拥有这样一种中立,但他远远不能作出有价值的陈述。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知道。他们的判断可能不够客观∶他们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尽量避免任何个人偏见,而这正是此类著作的困难之处。有时,在提到个人经历时,拥有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在撰写此书时,我曾倾向于匿名发表,只使用我的监狱号码。但在草稿完成时,我意识到,作为匿名出版物,本书将失去一半的价值;并且,我必须拥有勇气公开表达我的信念。因此,我没有删除任何段落,尽管我并不喜欢暴露主义。 我将有关从本书内容中提炼出纯粹理论的工作留给他人。这一工作可能会大大促进囚徒生活心理学的发展。这一开始于一战之后的研究,使得我们熟悉了“带刺铁丝网疾病”的症状。我们应当感谢二战,它丰富了我们的“大众精神病学”知识,〔如果需要,我可以引用由勒庞撰写的一本书中的众所周知的词语和题目〕因为战争给了我神经之战,战争给了我集中营。 由于这一故事涉及我作为一名普通囚徒的经历,十分重要的是,我必须提到,并非没有任何自豪地,除了最后几周之外,我在集中营中并没有被雇佣为精神病医生,或者甚至是医生。我的一些同行十分幸运地受雇于毫无紧张气氛的急救站,使用碎纸片打绷带。我的号码是119104,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铁路线上挖橱和铺设轨道。有一次,我的工作是独自一人为路面下的水管开挖一条壕沟。这一工作并非毫无报酬;正好在1944年圣诞节之前,我得到了一种所谓的“奖偿券”的礼物。它是由建筑公司向我们这些实际被卖作奴隶的人发行的∶公司向集中营当局支付每人每天多少钱的固定价格。这些奖偿券每张实际用去了公司50芬尼〔德国货币单位,相当于一马克的百分之一—译者注〕,通常在一周之后,每张可以换取6支香烟,尽管有时它们也可能失去效用。成为价值12支香烟的符号的拥有者,我非常自豪。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香烟可以换取12份汤。而12份汤有时可以暂时免除非常真实的饿死惩罚。 实际的吸烟特权是为那些能够获得每周定额奖偿券的大头领们所保留的;或者是为作为仓库或车间的工头的囚徒而保留的,因为他们可以收到一些为调换危险工作而贿赂的香烟。这一情况的惟一例外是那些失去生活愿望并想“享受”最后几天的囚徒。每当我们看到一位难友吸着自己的香烟时,我们就知道他放弃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并且一旦失去,这一愿望就几乎不可能重返。 冷漠、感情迟钝,以及人们不再关心任何事情的感觉,是产生于囚徒心理反应第二阶段的症状,并最终使他对于时时刻刻的殴打折磨无动于衷。通过这一无动于衷的感觉,囚徒们用一种非常必要的保护性外壳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稍有不敬,有时甚至毫无缘由,就会招来一顿殴打。例如,面包是在我们干活的地方分发的,而且,为了领取面包,我们还不得不排队。有一次,我后面的人站得稍微偏了一点。这一对称性的缺乏惹怒了党卫军。我不知道后面的队伍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意识到党卫军的存在,但是,我的头突然被猛击了两下。到了这时,我才看见党卫军正在我的侧面抡起他的棍棒。在这一时刻,最疼痛的并不是肉体〔而且它既适用于成人,也适用于儿童〕;它是由不公正、由彻底的不可理喻而造成的伤害。 十分奇怪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没有留下痕迹的打击甚至比留下痕迹的更加疼痛。有一次,我站立在暴风雪中的铁路上。天气虽然恶劣,但是我们仍要不停地干活。我卖力地用碎石修补路基,因为这是保持身体温暖的惟一办法。我停了下来,靠着铁锹喘了日气,也就一会儿的功夫,然而,倒霉的是,正在这时,看守转过身来,发现我在偷懒∶他对我的伤害不是来自于侮辱和拳打脚踢。这个看守认为,不值得向站在前面的这位衣衫破烂、瘦骨嶙峋的家伙说一句话,甚至不值得咒骂、相反地,他顽皮地捡起一块石头并向我扔了过来。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办法,用来吸引野兽注意,吆喝家畜干活,一种与你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的生物,以至于你甚至不愿意惩罚它。 打击中最疼痛的部分是打击所包括的侮辱。有一次,我们在结冰的轨道上抬着沉重的钢梁。如果一个人滑倒,不仅危及他的生命,而且所有抬同一根钢梁的人都会受到影响。我的一位年纪较大的朋友的臀部先天性脱臼。尽管如此,能够干活他仍然十分高兴,因为进行选择时,身体残疾的人几乎肯定要被送上死路。他抬着沉重的钢梁。在铁轨上一瘸一拐地走着,看起来几乎要倒下去,其他人也被拖拽着。当时,我没有参与抬钢梁,因此,我不加思索地跳起来帮助他。然而,我的脊背立即受到了重重的一击,并听到有人粗暴地申斥和命令我回到自己的位置。一分钟之前,打我的那位看守还抨击我们说,我们这些“猪锣”缺少合作精神。 有一次,在一片森林中,气温华氏2度,为了铺设水管,我们开始挖掘冻结得非常严实的土壤。但在当时,我的身体一作常虚弱。同来的人中有一位脸颊红润饱满的工头。他在寒冷的冬天里戴一双很温暖的手套。他一言不发地看了我很长一会,我感到麻烦就要来了,因为我面前的土墩表明了我的工作量。 于是他开口道∶“你这头猪猡,我一直在看着你!我来教你怎样干活!一直等到你用牙齿挖土——你会像野兽一样死去!两天之内我将要你完蛋!你一生从未干过活。你是干什么的?商人?” 我忍无可忍,但是,对于他的死亡威胁,我却不得不严肃对待。因此,我挺直身体并直接盯着他。“我是医生——专业人士。” “什么?你是医生?我想你一定从人们的口袋里捞了不少钱吧。” “说实在的,在为穷人开的诊所里,我的工作大多分文不取。”但我说得太多了。他像疯子一样吼叫着向我扑了过来,并一拳将我打倒。他喊叫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希望通过这一显然不值一提的故事说明,有时,看起来十分老练的囚徒有时也可能发怒——不是由于遭受毒打,而是为了与之相连的凌辱。那时,我热血冲向头部,是因为我不得不听一位对于生命一无所知的人对于我的生活说只道四,一位(我必须坦白∶以下在我离开现场之后我的囚徒所作的评沦,给了我孩子般的宽慰。〕“看起来庸俗粗鲁,以至于我的医院门诊部的护士都不愿让他进人候诊室”的家伙的评沦。〕 有幸的是,我的工作队的大头领对我一直不错。他喜欢我的原因在于,在走向工地的漫长路途中,我一直洗耳恭听他的爱情故事和婚姻麻烦。我对他的性格诊断和精神疗法建议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对我十分感激,这一态度对我是弥足珍贵。他为我保留了一个铺位。这一铺位紧挨着他,在我们这个通常由280人组成的铺位方阵的第一排。这一位置所带来的优势十分重要。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必须起来排队。大家都担心迟到,担心落在后面。这是因为,如果需要有人去做令人不快的工作,大头领就会站出来,通常会从后面几排挑选一些需要的人。这些人必须步行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陌生看守的指挥下从事令人畏俱的工作。有时,为了抓住偷奸耍滑者,大头领也会从前五排挑人。在精确无误的拳打脚踢下,所有的抗议和哀求慢慢地平息了,被挑选的受害者被喊叫和鞭打驭赶到了集合地点。 但是,只要大头领有向我倾诉的需求,这一厄运就不会落在我的身上。我将荣幸地永远占据与他为邻的铺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优势。当时,就像集中营中几乎所有的囚徒那样,我正患着水肿。我双脚肿大,脚上皮肤紧绷,以至于几乎不能弯下膝盖。为了使鞋能 够适应我的肿胀的双脚,我不得不让鞋带松散着。即使我有袜子,也没有袜子的空间。所以,我的一半裸露的脚总是湿的,鞋子里总是装满了雪。这当然会生冻疮。每迈一步都是真正的折磨。当我们行走在冰雪覆盖的土地上时,大块的冰雪冻结在我们的鞋子上。一次次地,人们滑倒在地,跟在后面的人绊倒在他们的头上。然后,这支队伍将停顿片刻。不久,看守就会动起手来,用枪托向囚徒的身上捣去,催促他们赶快起来。你的位置越靠近队伍的前面,你就越少受到必须停下来、然后为弥补时间面用疼痛双脚赶路的打搅。作为私下任命的尊敬的大头领的医生,我能够在队伍的第一排四平八稳地走着,心里自然感到非常高兴。 作为这一服务的额外报酬,我可以肯定,只要工地午餐有汤可分,在轮到我时,大头领就会将汤勺直接伸进汤桶的底部,捞出一些豌豆。这位大头领,一名前军官,甚至有勇气低声向曾经与我发生争执的工头说,他知道我将成为非同一般的千活好手。这样做似乎毫无用处,但他还是努力去挽救我的生命〔许多次中的一次,我曾经因此而获救〕。在我与工头发生冲突的那一天,他偷偷地把我派到了另一个工作队。 有些工头会同情我们,并尽力改善我们的处境,至少是在工地上。但是,即使他们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一名正常的工人可以做几倍于我们的一作,而且所用的时间更短。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正常工人并不以每天十又二分之一盎司的面包〔理论上的—实际上,我们常常吃得比这更少〕和一又三分之一品脱的汤生活;正常工人并不生活在我们不得不屈从的精神压力之下,没有家庭的消息,不知道他们是被送往了集中营还是直接被送进了毒气室;普通工人并不每时每刻地受到死亡的威胁。我曾经对一位心地善良的工头说,“如果你能在我学会修路所需一样长的时间内学会做脑部手术,我将对你敬若神明。”他咧嘴笑了。 第二阶段的主要症状,冷漠,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自我保护机制。现实暗淡无光,并且,所有的努力和所有的情感都集中于一种任务∶保全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非常典型的是,晚上,当囚徒们被驱赶着从工地回到集中营时,他们常常轻松地叹口气并说道,“唉,一天又过去了。” 非常容易理解的是,这样一种紧张状态,加上经常需要关注如何才能活下去的问题,迫使囚徒的内心生活降到了最原始的层次。我的几位曾受过精神分析法训练的集中营同事经常提到集中营囚徒的“退化”—一种向更原始精神生活的倒退。囚徒的希望和梦想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睡梦中。囚徒们经常梦见的是什么?是面包、蛋糕、香烟和舒适的热水澡。这些简单需求的难以满足导致他们在梦中寻求愿望的实现。这些梦是否有益,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做梦的人不得不从梦中醒来,面对集中营生活的现实,面对现实与梦幻之间的强烈对比。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天夜里,我是如何被一位囚徒朋友的呻岭声所惊醒的,他在梦中四肢乱动,很明显,他正在做恶梦。因为我一直同情做恶梦的或精神错乱的人,所以,我准备把这个可怜的家伙唤醒。突然,我抽回了正准备摇晃他的手,并因为我正要做的事情而惊恐不已。在那一时刻,我强烈地意识到,不管梦是多么的恐怖,它也比不了集中营的现实,而我却要让他回到恐怖的现实之中。 由于囚徒们极度的营养不良,对于食物的渴望自然成为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原始本能。让我们观察一下,当囚徒们碰巧在一起千活且无人严加看管时,多数囚徒都做了什么?他们将立刻开始探讨食物。一位囚徒问另一位正在他旁边干活的囚徒,他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然后,他们将交换菜谱,并着手为他们的聚餐—在遥远的将来,当他们获得解放并回到家时—准备菜谱。他们将反复讨论,描述它的一切细节,直到突然传来一声警告,通常以一种特别的暗语或号码的形式∶“看守来 了。” 我一直认为,这样讨论食物是十分危险的。当人们努力适应这些份量少民热量低的食物时,用这样详细而有影响力的美味去挑逗人的有机体,难道不是一种错误吗?尽管它能够提供大量的精神安慰,但是,这一幻觉在生理上却未必不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囚禁的后一阶段,我们每天的定量包括每天一次的稀汤和通常很小的一块面包。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额外补助”,包括四分之三盎司的人造黄油和一小片腊肠,或者一小片奶酪,或者一点蜂蜜,或者一汤匙稀薄的果酱。每天都有变化。这些食物在热量上绝对不够,尤其考虑到每天的繁重体力劳动,以及穿着单薄的衣服长时间站在野外。得到“特别看护”的病人—也就是那些被允许躺在棚屋里、不用离开集中营去干活的人—生活就更差了。 当最后一点皮下脂肪消失的时候,当我们看起来就像用皮肤和破布掩饰的骸镂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开始消耗自己的身体。生物体消耗自身的蛋白,肌肉逐渐消失了。然后,身体失去抵抗力。一个接一个地,我们棚屋仅剩的一些人开始死去。我们每个人都能相当精确地计算出下一次将轮到谁,他自己的死亡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多次观察之后,我们已经十分熟悉这些症状,并使得我们对于症状的判断具有相当的把握。我们相互之间轻声低语,“他活不r多久。”或者,“厂一次就轮到他了。”并目_,在我们每天寻找虱子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夜间着见我们自己的裸体时,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一身体,我的身体,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尸体了。我已经变成了什么?我只不过是在带刺铁丝网之后.拥挤在几座棚屋中的一群中的一员;每天某一部分由于它变得无生命而开始腐烂的一群中的一个。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每当囚徒获得一点空余时间时,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想到食物。这也许可以理解为,那些没有相同经历的人几乎无法想象,濒临饿死的人所经历的毁灭灵魂的思想斗争和意志力的冲突。他们几乎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将意味着什么∶在壕沟里站着挖土,盼望着上午九点半或十点—半小时的午餐时间—的哨音,因为这时将分配面包〔如果仍然能够供应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询问工头—如果他不是令人不悦的话—现在是几点钟;温存地抚摸上衣口袋中的面包,首先,用冻僵的手抚摸它,然后,籍下一点,将它放人u中,最后,用最后的一点意志力把它再次塞人口袋,暗暗发暂一定要坚持到下午。 在处理这一小块面包—在监禁的最后阶段,每天只分发一次—的某一方法是否具有意义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展开无休止的争论。在此问题「,大致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派主张立刻吃完。这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可以至少一天一次满足严重饥饿的剧痛,第二,可以防止面包被偷或丢失。另一派别采取不同的观点,主张将份额分成几份。最终,我加人了后一派别。 集中营生活24小时中最可怕的时刻是醒来的时候。当还处于夜间的时候,三声尖利的哨声无情地将我们从疲惫的睡眠中和梦中的希望中惊醒。然后,我们开始努力将因浮肿而酸胀的双脚用力塞进湿漉漉的鞋子中。而且,常常因一些诸如替代鞋带的电线突然折断等细小故障而呻吟和叹息。一天早晨,我听见一位一直表现得非常勇敢和自尊的囚徒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起来。这是因为,他的鞋子破了,无法再穿,最终只得赤脚走到冰雪覆盖的操场上。在这一可怕的时刻,我找到了一点小小的安慰;我从门袋里掏出了一小块面包,满怀喜悦地用力咀嚼起来。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