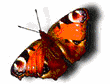|
对于局外人来说,要想理解集中营中对于人的生命的极度蔑视,是十分困难的。集中营的囚徒是老练的,然而,当集中营组织病人转移时,他们可能更加意识到这一对于人的存在的完全漠视。病人的瘦弱驱体被扔到两轮马车上,由囚徒们拉着,通常是在暴风雪之中,经过几英里的跋涉,到达下一个集中营。如果病人在出发后死去,也必须将他扔在车上——名单必须正确无误!名单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重要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囚徒号码。一个人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号码∶是死是活,都不重要;一个“号码”的死活完全无关紧要。这一号码和这一生命背后的东西就更不重要了∶这个人的命运、经历和姓名。在病人转移过程中,作为医生,我必须一路陪伴,从巴伐利亚的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囚徒需要转移,而他的兄弟不在这份名单上,因此必须留下米。这个年轻人苦苦乞求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集中营典狱官决定给予调换。当时有一位囚徒希望能够留下来,于是这位兄弟替代了这个人的位置。但是,名单必须准确无误!这很容易。于是,这位兄弟与这位囚徒交换了号码。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没有档案;然而,幸运的是,每个人都还拥有自己的身体,无论如何,身体还能呼吸。我们其他一切东西,例如悬挂在瘦骨嶙峋的骨架上的破衣服,只有当我们被安排参加病人转移时。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带着一种不知羞耻的好奇去观察即将离开的人,看看他们的上衣或鞋子是否比自己的更好。毕竟,他们的生命已经完结了。但是,那些留在集中营的人,他们仍然能够干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他们并不多愁善感。囚徒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看守的情绪——命运的玩物——这使得他们变得缺少人性,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环境的作用。
在组织病人向“休息集中营”转移时,由于需要一些医生,我的名字〔即我的号码〕出现在名单上。但是,没有人相信,转移的目的地是真正的休息集中营。几周之前,曾经准备了一次相同的转移。当时,每个人都认为,转移的目的地是毒气室。当集中营军官宣布,自愿参加夜班工作者可以把姓名从转移名单上划去,82名囚徒报了名。一刻钟之后,取消了这次转移,但这82名囚徒仍要上夜班。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来说,这意味着两周之内将会死亡。 现在,向休息集中营的转移又要组织了。没有人知道,这是否又是一个从病人中榨取最后一点工作的诡计——哪怕只有14天——它将走向毒气室,还是去真正的休息集中营?在十点差一刻时,一直对我另眼相待的医生主管偷偷地告诉我,“我在护理员办公室里得知。你还可以将你的名字从名单上划去;你可以在十点之前做这件事。” 我告诉他,这不关我的事;我学会了听天由命。我说,“我也许可以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他的眼中透出一丝同情的表情,似乎他已经知道……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似乎是一种告别,不是生命中的一次告别,而是与生命的告别。慢慢地,我走回了我的棚屋。在那里,我看到我的一位朋友正在等着我。 “你真的想跟他们一起走吗?”他悲哀地问道。 “是的。” 眼泪涌出了他的眼睛。我努力去安慰他。然后,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表达我的愿望∶“听着,奥托,如果我不能回家去见我的妻子,如果你能够看见她,那么请你告诉她,第一,我每时每刻都在与她说话。你记住了吗?第二,我比任何人都爱她。第三,在我娶她的短短一段时间超过了任何事情,甚至超越了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奥托。你现在哪里?你还活着吗?从我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又找到了你的妻子了吗?你还记得我是如何让你记住我的愿望的吗——逐字逐句地——尽管你的眼中充满了孩子般的眼泪。 第二天早晨,我与转移的队伍一起出发。这次转移不是一个诡计。我们不是开往毒气室,而是,确实开到了一个休息集中营。那些同情我的人仍然留在集中营。在那时,将要发生的饥荒甚至比我们新的集中营更严重。他们曾经试图保护自己,但是,他们只是堵死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在获得解放之后几个月的某一天,我遇到了一位来自于原先集中营的朋友。他告诉我,作为一名集中营的警察,他是如何寻找一块从一堆尸体上丢失的人肉。在一口罐子中,他查找到了正在煮着的人肉。同类相食的现象开始出现。我离开得正是时候。 这难道没有使人们想起德黑兰死鬼的故事吗?有一天,一位富有而强壮的波斯人与他的仆人在花园中散步。仆人哭着说,他刚才遇到了死鬼,死鬼威胁他。他乞求主人给他一匹最快的马,以便他能在当天晚上赶到德黑兰。主人表示同意,仆人飞身上马。在返回房间的路上,主人本人遇到了死鬼。主人质问死鬼,“你为什么要恐吓和威胁我的仆人?”“我没有威胁他;我只是对于他仍在这里而我们计划今天在德黑兰相见的情况表示惊讶。”死鬼说道。集中营的囚徒不敢作出任何决定或采取任何主动性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强烈地认为,命运是他的主人,他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它,相反地,他应听从命运的安排。另外,冷漠情绪在相当程度上也促成了囚徒的这种情感。有的时候,囚徒们必须作出具有生死性质的突然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囚徒们往往让命运为他作出选择。当囚徒们必须作出涉及逃避或不逃避的决定时,这一逃避责任的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必须下定决心的几分钟里——并且,它通常是几分钟的问题——他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他应该逃避吗?他应该冒险吗? 我也经历过这样一种折磨。随着战线的推进,我有了逃跑的机会。我的一位同事因履行医疗职责的需要而经常出访集中营外面的棚屋,他想逃跑并希望带我一起走。他以探访一位病情严重的病人,且需要专家建议为借口,将我带了出来。在集中营的外面,一个外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将为我们提供军服和文书。在最后时刻,我们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不得不重返集中营。利用这一机会,我们为自己准备了一些供给——几块腐烂的土豆——并且寻找一个麻布袋。 我们闯进了一个妇女集中营。它空无一人。所有的妇女都被送到了另外一个集中营;棚屋一片狼籍;很明显,许多妇女获得了供给并得以脱身。棚屋里有一些破布、稻草、腐败的食物和破裂的陶罐;有几只饭碗仍然完好无损,对我们来说,这将是一笔巨额财产。但是,我们决定不带走它们。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形势令人绝望,这些碗不仅用来盛放食物,而且还用作脸盆和马桶。〔按照规定,棚屋中严禁放置任何卫生器具。然而,一些人被迫打破这一规定,尤其是一些斑疹伤寒病人,他们非常虚弱,以至于甚至在别人的搀扶下也不能走出去。〕我作为一个屏障站立在门口,我的朋友则顺势闯进棚屋。不久,他在上衣里夹带了一块麻袋片回到了门外。他看见里面还有一块麻袋片,我可以带走它。所以,我们交换了位置。我钻了进去。我在垃圾中四处寻找,最终发现了一块麻袋片和一只牙刷,突然,在所被丢弃的东西中,我看见了一具妇女的尸体。 我跑回棚屋,收拾我的财产∶我的饭碗,一副从一位死亡的斑疹伤寒病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破手套,以及一些写着速记符号的纸片〔正如我以前所提到的,我在上面开始重新构思我在奥斯维辛丢失的手稿〕。我迅速地最后巡视一遍我的病人。他们躺在棚屋两边的朽木板上。我走近了我的唯一的同乡,他已濒临死亡,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能够挽救他的生命。我尽量地掩饰逃跑的念头,但是,我的难友似乎猜到了什么〔可能我表现得有些紧张〕。他用一种疲惫的声音问我,“你,也要出去吗?”我慌忙加以否认,但是发现难以避开他的 悲惨的表情。在转了一圈之后,我回到了他的身边。我再次地看到了绝望的表情,而且。我感到这一表情是一种谴责。当我告诉我的朋友我将跟他一起逃走时,这一痛苦的感情就变得分强烈。突然,我决定再一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跑出棚屋,告诉我的朋友我不能跟他一起走。在告诉他我将和我的病人一起留下来之后,这一痛苦的感觉立刻远离了我。我不知道未来的几天将发生什么,但我获得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内心平静。我回到了棚屋,坐在我的同乡脚头的木板上,努力地安慰他;然后,我跟其他人闲聊,努力使他们在神志昏迷中安静下来。 我们在集中营中的最后时刻到了。随着战线的日趋接近,几乎所有的囚徒都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大头领和厨师已经逃跑。这一天。一纸命令要求集中营在日落之前必须全部撤离。甚至为数不多的几个囚徒〔几位病人、医生和“护士”〕也必须撤离。到了夜里,集中营将被点燃。到了下午,接送病人的卡车还没有出现。相反地,集中营的大门突然关闭,看守严密监视着带刺铁丝网,防止任何人乘机逃脱。剩余的囚徒似乎注定要与集中营一起燃烧。于是,我和我的朋友第二次决定逃走。 我们接到命令,将三具尸体埋在铁丝网的外面。在集中营中,只有我们俩还有力量做这项工作。几乎所有其他人都躺在尚在使用的棚屋里,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地俯卧在床上。现在,我们开始制订计划∶在运出第一具尸体时,我们将把我的朋友的麻袋片藏在用作棺材的洗衣盆中,偷运出去。在运出第二具时,我们将带出我的麻袋片,第三趟,我们将伺机逃跑。前两趟,我们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回来之后,我等待着我的朋友,他正试图找到一片面包,以使我们在逃人森林的几天里能够有些东西充饥。我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由于他没有回来,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在三年的囚禁之后,我愉快地想象着自由,想象着跑向前线将会多么令人兴奋。但是,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 我的朋友刚刚回来,集中营的大门就打开了。一辆程亮的、铝灰色小汽车,上面画着巨大的十字,缓缓地开到了操场。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到了。从现在起,整个集中营和囚徒都将受到他的保护。这位代表住在附近的农庄,时刻监视着集中营,以防出现紧急事件。现在,谁还会操心逃跑的事呢?他从车卸下装着药品的箱子,并给大家散发香烟,我们接受着摄影,兴奋程度达到了顶点。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冒险跑向前线了。 兴奋之余,我们想起了第三具尸体。所以,我们把它抬到外面,并放到我们为这三具尸体挖掘的狭窄的墓穴中。陪伴我们的看守—一位不令人讨厌的人——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他看出,局势可能发生大转换,因此,争取赢得我们的好感。在向尸体上洒土之前,他加入了我们为死者举行的简短祈祷。在经历了过去的紧张与兴奋之后,在度过了与死神赛跑的最后几天之后,我们乞求和平的祈祷十分炽热,就像人类声曾经发出的一样。 所以,集中营的最后一天是在对于自由的盼望中度过的。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红十字会代表向我们保证、协议已经达成,集中营无需疏散。但在那天夜里,党卫军的卡车到了,并带来了清空集中营的命令。最后剩下的囚徒将被带到中心集中营,从那里,他们将在48钟头内被送往瑞士——用来交换战争囚犯。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些人就是党卫军。他们非常友好,好言好语地劝说我们不用害怕,只管上车,告诉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好运而高兴。那些身体还算强壮的人自己挤进了卡车,而病重体弱的则被费力地抬了上去。我和我的朋友——现在我们不再隐藏我们的麻袋片了——排在了最后一组。在这一组中,将挑选13个人等待乘坐最后一班车。两位医生主管清点出了必要的人数,但是忽略了我们二位。13个人上了卡车,我们感到惊讶、恼怒和失望,我们不得不留在后面。我向医生主管抱怨。他说,他疲劳过度且精神分散,以此为借口进行搪塞。他还说,他原认为我们还想逃跑。我们不耐烦地坐下来,将麻袋片披在背上,与其他剩下来的囚徒一起等待着最后一班卡车。我们还得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们在被人遗弃的看守室的垫子上躺了下来。最后几个钟头的兴奋使得我们不断在希望和失望之间颠簸,至此,我们已经精疲力竭。我们穿着衣服和鞋子,时刻等待着出发,最后,渐渐地睡着了。 来福枪和加农炮的声音唤醒了我们;飞弹的闪光照进了棚屋。医生主管冲进来,命令我们拿起地上的铺盖。一位囚徒穿着鞋子从我上面的床上跳下来,正好落在了我的肚子上。而这正好唤醒了我!然后,我们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战线已经到达了我们这里!射击声逐渐平息,天亮了。在外面,在集中营大门的旗杆上.一面白旗在风中飘动。
很多星期之后,我们发现,即使在最后时刻,命运仍然在同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剩余囚徒开玩笑。我们发现,人类的决定是如何地不确定,尤其在生和死的问题上。我曾见过一张摄于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小型集中营的照片。我们那些在那天晚上认为他们正迈向自由的朋友,就是被卡车带到了那个集中营,并且,正是在那里,他们被锁进了棚屋并被烧死在里面。在照片上,他们一半被烧焦的躯体依然清晰可辨。我再次想到了德黑兰的死鬼。除了作为一种防卫性机制的作用之外,囚徒的冷漠还来自于其他因素。饥饿和缺乏睡眠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正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并造成了囚徒精神状态的另外一种特征——易怒性。睡眠的缺乏部分出自于害虫的烦扰。由于普遍缺乏卫生保健设施,我们的异常拥挤的棚屋爬满了虱子。我们既没有尼古丁也没有咖啡因,也造成了人们的冷漠和易怒。 除了身体上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一些以某种情结出现的精神性原因。大多数囚徒都患有自卑情结。我们曾经是,或者想象自己是“大人物”。现在,我们被当成无足轻重的人。〔一个人的内心价值的意识植根于较高级的、较多精神性的东西,而且不会因集中营的生活而动摇。但是,又有多少自由人,更不用说是囚徒了,能够拥有它呢?〕如果不是有意识地思考它,普通囚徒就会感到自己完全堕落了,当人们仔细观察由集中营这一单一社会结构所提供的强烈对比时,这一点就会变得十分明显。较“显赫”的囚徒,如大头领、厨师、仓库管理员和集中营警察,作为一种普遍的情况,并不像多数囚徒那样,感到自己被贬低了,相反地—他们感到得到了提升!一些人甚至获得了荣耀感。嫉妒而牢骚满腹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一受到优待的少数人的精神反应,通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有时是玩笑。例如,我曾听见一位囚徒向另外一个人评价一位大头领:“看一看,当这个人只是一个大银行总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在这个世界里升迁得这样高,难道不是一种福气吗?” 每当受贬低的多数人同受提升的少数人发生冲突时〔这样的机会非常多,从分配食物开始〕,造成的后果通常是爆炸性的。因此,当这些精神紧张被增加时,一般的易怒〔它的身体原因在前文已经讨论〕就会变得非常激烈。并不奇怪的是,这一紧张常常以一种普遍的争斗而结束。由于囚徒们常常看见打斗场面,诉诸暴力的冲动就得到了增加。就我个人而言,当我发怒时,如果我又饿又累,我的拳头就会紧握起来。我经常是疲惫不堪,因为我们不得不整夜地生炉子——在斑疹伤寒的房子,这样做是允许的。然而,我所度过的最无聊的时刻是夜半时分。在这时,人们或者处于神志昏迷之中,或者在呼呼大睡。我可以直挺着身体躺在炉子的前面,并可以在由焦炭生出的火中烤一些偷窃来的马铃薯。但是,第二天,我感到更疲劳、更冷漠、更易怒。
在对于集中营囚徒的典型特征进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描述和解释时,我可能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人完全地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影响。〔在这一案例中,环境是集中营生活的独特结构,它迫使囚徒使之行为符合某一模式。〕但是,人的自由权呢?在人的行为和对于任何既定环境的反应中,存在着任何精神自由吗?一种使我们相信人只不过是许多条件的、环境的因素——如果它们在性质上是生物的、精神的或社会的—的产物的理论,是正确的吗?人仅仅只是这些因素的偶然产物吗?最重要的是,囚徒对于集中营单一世界的反应能够证明人不能逃避环境的影响吗?在面对这样一种环境时,人真的没有选择吗? 我们既可以根据经历也可以根据原则来回答这些问题。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表明,人确实具有一种行为的选择。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有时在性质上是英雄性的,它证明冷漠可以克服,易怒可以压制。甚至在精神和物质严重压迫的环境中,人仍然可以保留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的痕迹。 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在集中营中的人都还记得,有些人可以在棚屋中安慰别人,并拿出自己的最后一片面包。他们在数量上可能微乎其微,但是,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可以剥夺人的一切,但是,一件东西之外∶人的最后的自由——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方式。 而且,选择总是存在的。每时每刻地,提供机会做出决定,一种将决定你服从或不服从那些将剥夺你的自我、你的内心自由的决定;决定你是否将成为环境的玩物、放弃自由和尊严而成为典型的囚徒。 从这一角度来看,集中营囚徒的精神反应远远超出了对于某种物质的、社会的环境的表达。尽管诸如睡眠不足、食物医乏和各种各样的精神紧张等环境可能表明囚徒将以某种形式作出反应,但是,最后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囚徒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决定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集中营影响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看,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人都能决定他将成为什么——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甚至在集中营中他也可能保持人的尊严。托斯绥夫斯基曾经说,“我所惧怕的只有一件事情∶他的受难没有价值。”在我结识了集中营中的伟大受难者之后,这一话语经常进人我的脑海。他们在集中营的生活,他们的受难和死亡,证明了一个事实∶不能失去最后的内心自由。可以说,他们的受难是有价值的;他们承担痛苦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内在成就。正是这一精神自由——它不能被剥夺——使得人的生命有意义、有目标。 一种积极的生活将赋予人们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实现价值的机会。而一种消极的享乐生活将给他带来在体验美、艺术或自然等方面的满足。但是,在既没有创造也没有享受,只承认一种较高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即,在人对于他的存在、一种受到外在力量限制的存在的态度方面——的生活中,同样存在着目的∶他不能享有一种创造性生活或享受性生活。但是,具有意义的不只是创造和享受。如果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意义,那么,这一意义也必然存在于痛苦之中。痛苦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就像生和死一样。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是不完整的。 人们接受命运及其他所带来的所有苦难的方式,以及他选择生活道路的方式,使他获得了足够的机会——甚至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向他的生活增添更深刻的意义。他可能保持勇敢、自尊和无私。或者,在激烈的自我保护斗争中,他可能忘记了人的尊严,并只是变成了动物。在这里,存在着或者利用或者放弃,一种困难形势可能赋予他的、赢得道德价值观的机会。并且,这决定了他的受难是否具有价值。 不要认为这些想法只存在于天堂而与真实生活无关。真实情况是,只有一些人能够达到这徉高的道德标准。在囚徒中,只有一些人保持了他们的全部内心自由,并获得了其痛苦赋子的价值,但是,甚至一个这样的例子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心力量可能使他超越外部命运。这样的人并不仅仅存在于集中营中。在任何地方人们都面对着命运,面对着通过痛苦获得一些东西的机会。 例如,一些病人——尤其是无法治愈的——的命运。我曾经读到一封年轻病人写来的信。在信中,他告诉一位朋友,他刚刚发现他将不久于人世,甚至手术也无济于事。他进一步写道,他记得,他看过一部电影,描述一位年轻人以勇敢和自尊的方式等待着死亡。这个男孩认为,这样面对是一件伟大的成就。现在——他写道命运给他提供了一个相同的机会。 我们这些在几年前看过电影《重生》——取自托尔斯泰的一本书—的人,可能有着相似的看法。这里存在着伟大的命运和伟大的人。在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伟大的命运;没有取得伟大成就的机会。电影之后,我们去了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对着一杯咖啡和一份三明治,我们忘记了曾经进人我们脑海中的奇怪的哲学思想。但是,当我们自己面对一种伟大的命运,面对用相同的伟大精神来迎接挑战的决定时,到了那时,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很早以前曾经做出的幼稚的决心,并且,我们失败了。 也许在某一天,我们将再次观看相同的或者相似的电影。但是,到了那时,其他画面可能同时在我们的内部眼前展开;一些有关人们在生活中获得的比一场多愁善感的电影所表达的更多的人们的画面。一些有关一个人的内心伟大的细节可能进人到人的思想,就像一位我亲眼目睹她的死亡的年轻妇女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内容不多,而且听起来就像是我自己杜撰而成的;但是,对我来言,它是一首诗。 这位年轻的妇女知道她将在最近几天中死去。尽管她早已知道,但是,当我跟她说话时,她非常高兴。“我很感激命运给予我如此沉重的打击,”她告诉我,“在以前的生活中,我被宠坏了,从不严肃地对待精神上的成就。”她指着棚屋的窗户,继续说道,“这棵树是我孤独时的惟一朋友。”通过这扇窗户,她只能看见栗树的一棵枝娅,树枝上开着两朵花。“我经常跟这棵树对话,”她对我说。我非常惊讶,不知道如何对待她的话。她精神错乱了吗?我急切地询何她树是否作了回答。“是的。”它对她说了什么?她答道,“它对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我们已经说过,最终对于囚徒的内心自我状态发生作用的与其说是不胜枚举的心理原因,不如说是自由决定的结果。对于囚徒的心理观察表明,只有那些任其道德和精神自我的内心支柱沉沦的人,才会完全接受集中营恶化的影响。现在,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或者应该,构成什么样的“内心支柱”? 当以前的囚徒撰写或谈起他们的经历时,他们都认为,最为抑郁的影响是,囚徒不知道他的刑期到底有多长。他们无法得知释放的日期。〔在我们的集中营中,甚至无法谈论这一话题。〕实际上,囚徒的刑期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是无限的。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研究者指出,集中营的生活可以称做是“暂时性存在”。我们可以加经补充,将它定义为“不知期限的暂时性存在”。 新来者通常对于集中营的情况一无所知。那些从其他集中营回来的人被迫保持沉默,并且从一些集中营没有人回来。在进入集中的那一刻,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一种变化。随着不确定的结束,产生了目的的不确定。人们无法预测,这一存在的方式是否或者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拉丁语finis具有两重含义∶一种是终结或完结,另一种是将要达到的目标。一个人如果不能看见“临时存在”尽头,他就不能看到生命的最终目的,不能瞄准生命的最终目标。与正常生活中的人相比,他不再为未来而生活。因此。他的内心生活的结构全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我们从生活其他领域可以得知的衰落情景。例如,失业的工人就处于相似的环境中。他的存在变成临时性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再能够为未来而生活,或者瞄准一个目标。有关煤矿失业工人的研究表明,它们感受着一种特殊的畸形时间——内心时间这是失业状态的一个后果。囚徒也遭受这样一种奇怪的“时间经历”。在集中营中,一个小的时间单位,例如一天,充斥着几个钟头的折磨和疲乏,看起来似乎无边无尽。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可能是一周,似乎很快就已经过去。当我说,在集中营中一天比一周持续更长时,我的难友表示赞同。我们的时间经历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想起了托马斯·曼恩的《魔法山》。它包含了一些非常尖锐的心理评论。曼恩研究了那些处于一种类似心理状态中即在疗养院中不知道何时得以解脱的肺结核病人的精神发展。他们经历着同样的存在——没有未来和没有日标。 一位曾经跟随新来囚徒的队伍从火车站步行到集中营的囚徒在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感到,他似乎正行走在他自己的葬礼上。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似乎毫无前途。他认为,生命已经终结,他似乎已经死亡。这一无生命的感觉由于其他原因而进一步强化∶在时间上,它是人们深刻体会到的囚禁时间的无限;在空间上,是监狱空间的狭小。带刺铁丝网外面的任何事物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不可达到,并在一些方面,是不真实的。外面的事物和人,那里的所有正常生活,在囚徒看来,都有着可怕的一面。也就是说,外面的生活,就他所能看见的,在他看来,就像是一位死人从另一世界所看到的东西。 那些由于不能看到任何未来目标而任凭自己堕落的人,常常陷人对于过去的回忆之中。我们已经提到的,存在着一种趋势,回忆过去,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使得带有所有一切恐怖的现在变得更少真实。但是,在对于现实存在的回避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它使人容易忽视那些能够使集中营生活变得积极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确实存在。在使得囚徒丧失生活支柱的各种原因中,把“暂时性存在”看做是不真实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任何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这样的人忘记了,常常正是这些异常困难的外部环境向人们提供了在精神上超越自我的机会。与把集中营的困难看做是一种对于内心力量的考验相反,他们并不严肃地对待生活,而是把它们看做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事情。他们更愿意闭起眼睛,生活在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达到伟大的精神高度。一些人虽然在现实世界中遭受到明显的失败和死亡,但是,他们还是获得了实现人类伟大的机会。一种他们在普通环境下永远也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平庸而又缺乏热情的,可运用傅斯麦的话的描述他们,“生活就像在牙科诊所。你总是认为,最坏的还会来到,但是它已经过去了。”把这句话变化一下,我们可以说,集中营的大多数人相信,真正的生活机会已经过去。然而,实际上仍然存在着机会和挑战。人们可以从这些经历中取胜,把生活转化成为内种内心的胜利,否则,人们可能忽视这些挑战,只是无所事事地活着,大多数囚徒就是这样做的。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