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一个狱警过来打开了拘留室的门,又把三个常规问题问了一遍,然后带我离开。我又被剪短了头发,然后被拍下了正面和侧面的照片,接着按了指印。又回到了拘留室。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叫出来,接受登记,然后再次被锁在囚室里。一会儿过后,我被带了出来,被命令脱光衣服,然后进行常规体检。我花了一点时间来适应常规体检,因为就像俄罗斯其他地方一样,监狱里的医生大多是女性。不过,她们的整套工作沉静而高效,甚至有些乏味,所以我很快就学会了接受她们的探听和搜身,就像在普通体检中一样。
体检结束后,我的衣服被扔进消毒室,在高温下烘烤了一个小时,那温度高得把它们都烤黑了。与此同时,我全身赤裸地被带回囚室,在那里等自己的衣服。由于囚室的体检和其它常规程序的间隔很长,它们用去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我被领下楼走入长长的走廊,接着又上了几层楼,在我进入一间牢房前,天就已经快亮了。

齐赛克神父的一张监狱登记照
因为这幢建筑是个监狱,所以我称它为“牢房”。不过,它实际上更像一个酒店的房间:小巧而整洁,十分干净,有擦得锃亮的木质地板,还有粉刷过的墙壁和天花板,房间中央一盏裸露的灯泡为整个房间提供照明。一堵墙的格栅后面有一块暖气片,但它们似乎没有发出多少热量。房间角落里有一张床,上面放着干净的床单、被子和枕头。除此之外,仅剩的家具是靠近门边的角落里的一个带盖子的马桶(параша)。房间里有一扇窗子,大小是酒店房间的标准尺寸,后来我发现卢比扬卡曾是一家酒店,但它如今被一块巨大的铁皮完全封住了。如果我站在窗前,那么能看到的唯一风景就是透过铁皮的“口子”看到的一线天空,所谓的“口子”也就是铁皮顶到窗框而发生偏斜的地方。门上有一个圆形的窥视孔,狱警能透过它看到房间内部,而狱警侧的窥视孔则有一个防止囚犯看到外面的铰链盖子。
最初的搜身结束后几分钟,在我熟悉了新环境后,一股深重的倦怠感笼罩了我。我又困又饿又冷,尽管暖气片的热量微弱到根本无法取暖,但我还是很想睡觉。我开始在那个6×10英尺小房间的墙与床之间徘徊。我有时能听到鸣钟报时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发出的。
之后,随着早上7点的钟声响起,我开始听到走廊里的动静。突然,我听见门口狱警的声音。和卢比扬卡的大多数狱警一样,那是一名女性,她拿来了一份卢比扬卡的早餐,在我看来这是一顿献给神灵的盛宴——400克(3/4磅)的面包、半勺糖和一杯开水(кипяток)——这便是一成不变的卢比扬卡早餐。此时,我已经超过三十六个小时没有进食了。我坐在床上将面包撕成几大块,然后肆意咀嚼起来。
后来,我在卢比扬卡学会了省吃俭用,还学会了怎么悠闲地享用早餐,但此时此刻我已经快饿死了。在吞咽面包的间隙,我把几块糖混在热水中,一口喝了下去,甘甜的糖水混合物令我感到温暖。我后来还知道可以敲门让狱警帮忙续杯,借此获得更多开水。但那天早上,我在享用完面包、方糖和热水后就没有要求更多了。我依旧很饿,但这是我两天多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温暖,第一次感觉自己还是人。
不过老实说,我吃完早饭后的第一个念想就是晚饭。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在狱警来把铁皮杯收走后,我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徘徊,一是为了取暖,二是为了活动一下身体。睡觉在白天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你想躺下,差不多立刻就会被狱警发现,她会命令你起床。卢比扬卡的每条走廊里只有五六个牢房,有狱警对其进行不间断的检查。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仍旧疲惫不堪,也有点茫然,于是就这样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不断冥思苦想,听着每隔一刻钟就响起的钟声。
直到午后的某个时刻才有人来打扰我。我又听见了走廊里的声音,那是碗碟互相撞击的声响,如同巴甫洛夫的狗一般,我的唾液起了反应。终于,狱警将我的牢房门打开,递给我一个盛着汤的铁皮碗和一把铝制汤匙。那汤很稀,里面有几粒被我们称为“玛加拉”(Магара)的谷物,颗粒小得跟鸟食差不多。汤汁闻上去有一股鱼的气味,碗底还有几根骨头。我在彼尔姆的监狱里听说骨头对人有好处,能使人保持健壮,所以我就把汤里包括骨头在内的一切东西都吃下去了。我仅仅是把它们放在牙间磨成粉末,然后混在一口汤里喝下去。我还没等到把汤匙舔干净,就开始考虑晚饭的事了。
那天下午有一段二十分钟的活动时间,期间狱警会带我下楼到院子里散步。每天的活动时间都不一样,早至上午八点,晚至下午六点,这取决于狱警是从监狱的上层还是下层开始。我并不想去院子里,因为我的身体刚刚暖和起来,而监狱院子里的空气又冷。而且,我身上只穿了轻薄的裤子和外套,那是我从丘索沃伊一直穿到现在的衣服。

卢比扬卡,苏联情报机构所在地
晚饭时间是下午6点。五点半以后,我又听到走廊上传来碗碟的哗啦声,于是不耐烦地等待脚步声、钥匙在锁上的响声和门栓的撞击声。终于,狱警递上了同样的铁皮汤碗,这一次,碗里装着两三匙麦粥。换言之,卢比扬卡的菜式和彼尔姆监狱的菜式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俄罗斯监狱的伙食就少有变化。晚上的伙食就是两三匙麦粥。我学会了细嚼慢咽,几乎是一粒一粒地品尝,然后用手指在汤碗里滑动,舔到碗里只剩下闪亮的碗壁。
晚饭后约一个小时,狱警开始把走廊上的囚犯一个个带到厕所。和体检一样,这又是一个需要花时间适应的流程,因为即便在厕所里,狱警也会通过窥视孔注视你。厕所里只有地板上的一个洞、洞两侧用于落脚的凹痕以及用来支撑身体的墙壁。凡是在欧洲旅行过的人,都会了解我的描述。除了感觉自己每时每刻被注视着之外,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牢房里有水龙头可以用来洗漱,角落里有一个大污水盆,你可以用它清洗拿过去的马桶,那里还有一罐用于清洗的消毒液。
一切都必须迅速完成。如果我在厕所里呆了超过两分钟,狱警就会拍门叫我快点。之后,我又回到牢房开始了无休止的徘徊,一直持续到10点的就寝时间。灯会一整夜都亮着,除非典狱长或审讯员特许某人关上天花板上的灯,只留门上的蓝色应急小灯亮着。不过我在那天晚上顺利地入睡了,因为我已经有四十八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当就寝的信号传来时,我赶紧脱掉衣服,爬到干净的被单之间,然后把薄薄的毯子披在肩上。床垫很薄,薄得能让我感觉到后背下方的铁条,每当我翻身试着让自己舒服一点时,铁条就会戳到我的肋骨。
我做了晩祷,然后躺了一会儿,陷入万千思绪之中。此刻,我最想知道的是接下来自己会遇到什么。我无法相信自己竟如此重要,以至于经过彼尔姆数月疲劳的审讯后,他们还得将我押到莫斯科,我不停地寻找一个理由,以便对自己所受的特殊处置作出解释,但没能找到。我不断回想自己在彼尔姆所受的几次审讯,想得头都痛了起来,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再次于天主的圣意中求得庇护。我沉浸在他的护佑之中,然后睡着了。
第二天的白昼从早上五点半开始。铃声响起,片刻后,狱警开门喊了一声:“起来!”(Подъем!)。她没听到应答的声音,于是又喊了一声,然后走过来复查。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被依次带去厕所,然后返回牢房等待早餐。七点到了,但早餐没有送来。根据过往的经验,我知道早餐时间同其它用餐时间或者活动时间一样,可能在早上7点到8点半之间的某个时间轮到你,具体时间取决于狱警从监狱的哪一头开始送餐。监狱中的经验让我希望早餐来的越晚越好,这样一来等待晚餐的时间就会缩短。
好几天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急切地想知道自己来这里是要做什么,想弄清楚我将遇到什么事。由于狱警不能和囚犯谈话,所以我无从得知接下来发生的事,能做的无非是等待、徘徊、祈祷,或者不停地思考同样的问题,回忆自己在彼尔姆所受的审讯,寻找审讯中可能与接下来的事态有关的迹象或线索。最后,经过了沉思和忧虑,我将自己在离开彼尔姆时得知的一切都整理清楚了:我是一名政治犯,根据58:10:2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
经过数日的焦急等待,我在某天晚上听到了门闩的撞击声,从酣睡中醒来。凡是在夜间被突然惊醒的人都会明白这种感觉,我猜这是心理作用的一环,因为它能使你立即进入防备状态。狱警穿的是特制布鞋,所以直到他们快到门外时,你才会听到他们走近了。当你在睡觉时,通常首先听到的就是门闩回弹的声音,然后你便会在紧张和困惑中醒来。
那天晚上,狱警又问了我三个常规问题——姓名、生日、指控,然后她说:”做好准备!” 我匆忙穿好衣服,试图理清思路,让自己尽可能做好准备以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但是我完全找不着北,可是说得上是茫然无措。狱警把我带出牢房,按照惯例让我面抵墙站好,双手背在身后,与此同时她给房门上锁。随后,我们沿着走廊前进,快速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每到一扇门前,我就被逼着面抵墙站立。如果有人沿走廊向我们走来,我就会被匆忙地推到墙边,或者被推到一个角落里,并被警告在那些人通过前不要东张西望。
走过几条走廊,上了几层楼,我们来到了审讯室。尽管是在夜晚,接待室里仍有两三个秘书在工作。克格勃的人时不时从我身边经过,用懒散的眼光瞟了我几眼。狱警将我押往接待室外的房间,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内部相当舒适,锃亮的地板中央有一张地毯。房间里有两扇窗子,窗子上都安装了闭合的百叶窗,两扇窗中间有一张光亮如镜的大办公桌,桌后坐着审讯员——我进入房间时,他正在翻阅一些资料。房间里还有几把填充椅,一堵墙的边上放着一张长椅,角落里放着三四个绿色文件箱。
审讯员是一个身着克格勃制服的中年男子,他坚毅的面容此刻颇为疲惫,一头黑发从两鬓开始变得稀疏。他不置可否地跟我打起招呼,仿佛这就是他一天全部的工作,然后叫我坐下。我坐了下来,但放松不起来。在这样的审讯开始时,心理层面的紧张感十分强烈。因为你要为未知的发问做好准备,你的身体紧绷起来,掌心开始微微出汗。根据他的面容和房间的外观,我明白这位审讯员是个专家。
在此次审讯期间,他的语气柔和,而且总是就事论事,就像人事经理在给求职者做面试一样。他从我的名字、生日和指控开始说起,接着详细地讲起我至今为止的所有经历。在详细的询问开始前,他漫不经心地提醒我,他已经掌握了我之前受审中的所有细节,外加几次独立调查的结果。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已经对我了如指掌。这只是一场预审,如果我直接说实话,一切都会更加顺利。
我起初对他说,我是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利宾斯基,出生于1910年11月4日,根据58: 10: 2受到指控。” 他抬起头来,脸上浮现出一丝恼怒的神色,仿佛是在想别的事情时被打乱了思路。“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说,“你是瓦尔特·齐赛克神父,一位来自阿伯丁的耶稣会士,1904年11月4日出生于美国。让我们把所有的伪装都放下,尽量不要在完成你的口供时搞出乱子,可以吗?”
我再次从头讲起自己的经历。然而,他经常在中途打断,然后问一些问题——我从未怀疑他们早就知道我会怎么回答,结果我们的审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问答环节,他会一一询问细节,而我则回答 “是”或“不是”,尽可能少做解释。
这个审讯员并不算特别固执,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尽职尽责,希望得到一点配合的人。那晚他好像在想什么别的事情,所以仅仅是把以前审讯中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他对照桌上的报告把我的经历一点点写下来,还会询问一些特别的细节。当我们完成了基本的口供,将他事无巨细的质问回答完毕时,天已经亮了,我能看到阳光透过他身后的百叶窗照射进来。他补充说,很快就会再传唤我,让我有机会填写遗漏的细节。
回牢房吃完早餐后,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苦苦思索那场审讯。他们掌握的我的背景资料如此之多,简直令我震惊。我不明白他们如何知道这么多,而且是在很久之后才弄清这件事。后来一个审讯员告诉我,他从马卡尔神父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马卡尔是在越过匈牙利边境进入被占领的波兰时被捕的,当时我和涅斯捷罗夫正在丘索沃伊工作(这件事说明马卡尔并未如他所答应的那样加入我们,也解释了我们被捕前一直受到监视的原因)。为了让我相信他所言不虚,那个审讯员给我看了马卡尔被捕时拍的照片。我几乎认不出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格鲁吉亚人:他的脸瘦弱而憔悴,看上去好像消瘦了不少。但毫无疑问,那个人确实是马卡尔。
正如我先前所说,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这一切的。但在那天早上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彻底被搞糊涂了。我推测或许是涅斯捷罗夫说了实话,又或许我们自阿伯丁开始就一直受到监视,却没有对自己受到的监视产生怀疑。我无从得知这一切的答案。尽管事情在随后的审讯中变得清晰了许多,但那天早上我真的是胆颤心惊。
我以为自己当晚会再一次受到传唤,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之后的几天也安然无事。时间拖了几个星期,依然没有人传唤我。于是,我为自己制定了一套日程安排,开始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像在故乡的耶稣会修院一样。早晨一起床,我会先做晨祷,洗漱完毕后再做一个小时的默想。正如我在耶稣会大部分时间遵守的日程安排那样,我五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餐,日子开始变得模式化。
吃完早餐后,我就会凭记忆做弥撒,换句话说,由于没法做真正的弥撒,我会把所有的祷文念出来。当克里姆林宫报时的钟声在早中晚响起时,我都会念《三钟经》(Angelus)。午餐前,我会做午间省察(examen);在夜晚,我会在睡觉前按照圣依纳爵的《神操》做晚间省察,总结晨间默想的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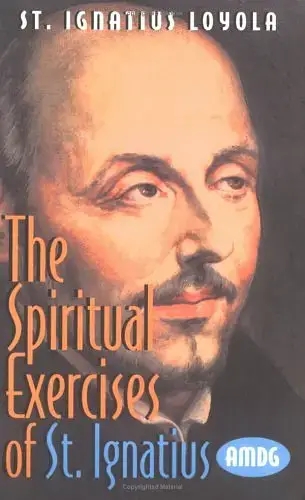
耶稣会士的必修课《神操》
每天下午,我用波兰语、拉丁语和俄语念三串玫瑰经以代替日课。晚饭后,我花一晚上时间凭记忆背诵祷文和圣乐,甚至将它们大声吟诵出来:《基督之魂》(Anima Christi)、《伏求造物圣神降临》(Veni creator)、《母后万福经》(Salve Regina)、《天主圣神求你降临》(Veni Sancte Spiritus),尤其是《末日经》(Dies Irae)和《垂怜经》(Miserere)——全都是我们作修生时在修院中背诵过的,还有我们在耶稣会的几年中唱过的圣乐,以及我幼时在家乡学过的祷文。
有时,我会花上几个小时努力将忘记的祷文回想起来,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直到念对为止。在这些祈祷的时间里,我也会编写自己的祷文与天主直接对话,向他寻求帮助,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接受天主赋予我的旨意,相信上主的天意(His providence)会助我渡过一切难关。
在晨祷之后和漫长的下午,我还会背诵一些自己能记住的诗歌。华兹华斯的《我们七个》,或者雪莱的《西风颂》,或者伯恩斯的《给一只小老鼠的小诗》,我觉得这首诗十分贴切我当前的处境,而且它一直是我的最爱。偶尔我也会即兴编一些关于某个主题的讲道或演讲,就这样大声地扯淡和自言自语,为的是令自己保持清醒。
我还喜欢尝试俄国常见的那种长篇笑话:比如“斯大林造访集体农庄(колхоз)”。我会试着编写出最可笑的问答,目的仅仅是让自己笑起来。我想象农民们向斯大林讨要面包、拖拉机或牛奶,对斯大林说他们有多饿。扮作“乔叔叔”的我会冷酷地回答“这不会是他们第一次挨饿”,或者劝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五年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等等。这有点傻里傻气的,但它有助于破解可能出现的抑郁期。
(译者:oblivious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