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判决后回到牢房,无法入眠。我用一整个不眠之夜回想过去发生的事,猜测假如自己先前承认他们对我的一些指控,那又会发生什么。我猜想,判决是不是在我被捕时就已经定好了。我还开始想象劳改营的样子,我曾经从其他囚犯那里听到过各种各样有关劳改营的故事和传言。我想的是,至少我能再次见到人群,即便那里的工作再辛苦,我也会欣然接受,因为那总好过被关在牢房里。如今判决已经下来了,我很焦虑,不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我明白天主会照顾我,却从未想过,自己还要等上四年才能看到西伯利亚。
两天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第三天早上,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到了我的牢房。那是监狱的图书管理员,她亲切地跟我寒暄了几句,问道:“你想看点书吗,同志(товарищ)?”。
“什么?”我说,“噢,当然,当然!”
“好的,你每次可以借出一本书,如果你想要的话,我每周都会回来更换书籍。如果你把书看完了,只要让狱警通知我,我就会过来换书,这样你就不用等上一整周了。”
就这样,我在“卢比扬卡大学”的“博士阶段”开始了。为了提高俄语水平,我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我从托尔斯泰开始,基本上把他的全部作品都读过了。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新的日程表:中午之前做灵性方面的义务,然后一直阅读到晚饭时间。晚饭前,我会做日间省察,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十二点响起时,我念《三钟经》。午饭后,我用波兰语、俄语和拉丁语各念一串玫瑰经,然后再去读书,一直读到外出活动时间或上厕所时间,吃完晚饭后,我会凭记忆做晚祷,吟唱圣乐。然后再次回到书本中,一直读到就寝时间。
那就是我每日的日程安排,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人打扰我。除了监狱长偶尔会来探望我,以及每周一次的健康检查和寄生虫检测外,我没有见过狱警以外的人。事实上,我成了一个与祈祷和书本为伴的隐士。我发现自己甚至都忘记怎么说话了! 不管是偶尔与医生交谈时,还是在监狱长不定期来探望时,我说话总是结结巴巴的。
除了每天二十分钟的活动时间外,我还试着通过每天两次擦地板来保持自己的活力。反正我们在卢比扬卡每天都要擦一次地板,但许多囚犯只是在口头上答应,而我却真的出力去干这件事,目的仅仅是享受活动的乐趣。卢比扬卡的地板是用优质的橡木制成的,带有一种美丽的光泽。我先用柔软的抹布清除地板上的灰尘,然后用大支的蜡棒打上蜡,接着再用包着布的重熨斗和一些油脂把地板擦得锃亮。
如今手头有了时间,我也开始修补衣服了,它们自我在丘索沃伊被捕以来就一直穿在身上,现在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监狱里严禁针、刀片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但我有时会从汤里捞出一些大鱼骨,在床的铁条上将它磨成可以使用的针。在读书时,我还用铁条和指甲把书上的订书针松开,然后把订书针在床上磨得很锋利,之后用它在骨头上刺出一个洞。接下来我就会从自己的衬衫、内衣或袜子上拉出一根线,然后开始练习裁缝的手艺。自然,那根针一经发现就会被没收,尤其是在两周一次的全面搜查中。这说明了卢比扬卡搜查效率很高,连鱼骨针这么小的东西,就算是藏在房间里或身上也会被他们搜到。
所以,在卢比扬卡四年的“大学教育”期间,我不仅重视精神生活,也重视物质生活。每天,我至少做四十五分钟的健身操,让自己的身体和阅读的思维一样活跃。我尽可能让自己和衣服保持清洁,使房间看起来一尘不染。我决意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克服自己的懒散,以保持自己的人性以及精神方面的警觉,不让监狱里日复一日的琐事使我消沉下去。正如囚犯中间流行的那句话,我“无言却快乐” 。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我一直记着时刻和日子,尽己所能记住了教会的所有瞻礼日,并用自己记住的或自创的特殊祷文庆祝它们。
我带着复仇的心态学习俄罗斯文学。除了托尔斯泰,我还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列斯科夫,以及杰克·伦敦、狄更斯、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许多作品,甚至还有俄文版的《你往何处去》。此外,我读了不少俄国历史,还有年老的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为拿破仑撰写的一本新传记——这本书是他在狱中写成的。在我的印象中,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拿破仑生活中的宗教活动——他的加冕礼、婚姻和后事等等,不但被省略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我惊叹于此书高超的技巧,更能理解为无产阶级重写历史意味着什么,也明白了它是怎样使年轻人听不到任何与天主有关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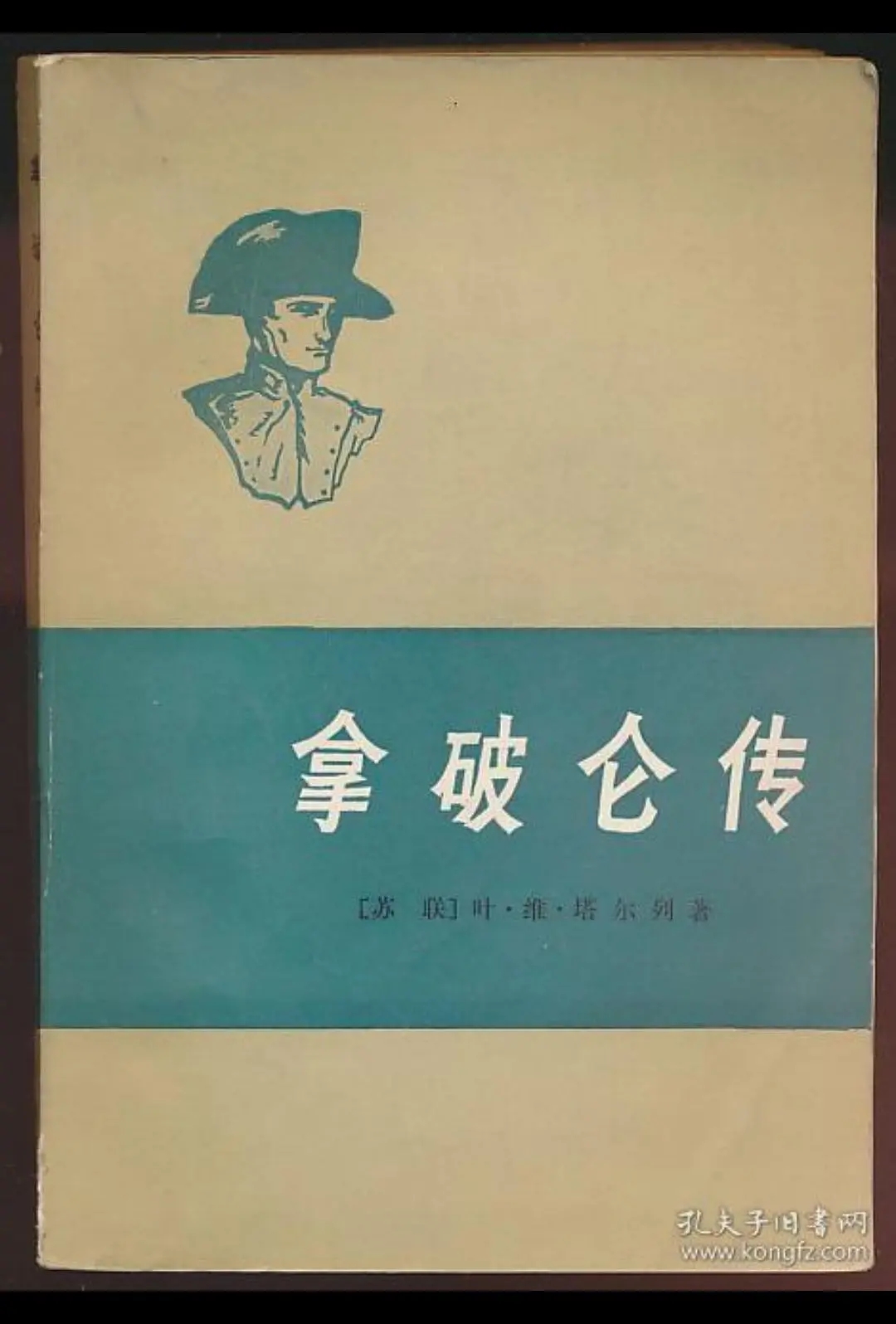
此时我所读的另一本书也给我留下了类似的印象。那是一本俄罗斯东正教会研究的皇皇巨著,是在“新任莫斯科及
然而,书的最后有一篇文章,据称是由一位东正教的教士所写。这篇文章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猛烈抨击,并且刻意使用了一种鼓吹仇恨和报复的文风。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深感震惊,乃至确信它不可能是真的。一位司祭有自己的圣召理念,他所受的训练是在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像小孩子一样彼此相爱”下进行的,但我根本无法将这些理念与那篇文章中的仇恨式宣传相调和。对我来说,那篇文章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政府短暂地放松了对教会的压制,重开了上千座教堂,神职人员开始参与公共生活,协助募集资金和物资,部分神父甚至拿起武器参战。
随着我对俄语的掌握程度不断提高,我差不多以每天一本书的速度在阅读。我不断地阅读,虽然没有眼镜,但眼睛却丝毫没有妨碍过我。在图书馆员的建议下,我还阅读了《列宁哲学百科全书》。我在书里找到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共产主义的定义,还把它背了下来。不久后的一天,正当审讯员和我在紧张的答问间不顾规定争论起来,我当着他的面引用了列宁对理想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下的定义。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咧嘴一笑:“啊,可那是什么时候?当然不是在你我的有生之年,也可能要等上100年。”他轻轻一挥手就把这个话题打断了。
除了每周一次的体检和常规检查外,我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任何事物的打扰——除了饥饿。事实上,在判决后,我的口粮配额增加了。我现在所用的是标准的劳改营配额——早上有600克的面包,中午有半升汤,晚上有一碗麦粥,有时还有一片鲱鱼或土豆。严格来讲我现在不是卢比扬卡的囚犯,而是劳改营的“拘留犯”。结果就是,我得到的食物前所未有地多,但不知为何,我发现自己对食物的念想也比以往都要多。
有时候,当我一边来回踱步一边看书的时候,会沉浸在晚餐的念想中。我听着钟声,变得紧张起来,想知道离吃饭时间还有多久。我根本无法摆脱这个念想。我越是想专注于书籍或其他事物,注意力似乎就越是集中到自己的饥饿感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做一些活动——对我来说,这通常意味着磨洗地板,我会凭借旺盛的精力,有条不紊地做这项工作,这样才能忘却时间的流逝以及对食物的念想。
突然,在一年零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意外地被叫出来带到了审讯室。我很反感。一想到在审讯结束后又要继续审讯,我就气恨难消。此外,我越来越习惯于隐士生活,对这种侵犯我隐私的行为心生厌烦。
这是另一位审讯员,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四十五岁左右,有一头深棕色的头发,五官端正,身着便装。他相当友善,但是很认真,总是让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司机。在这一类审讯开始的时候,我总是会感觉到内心的紧张和厌烦情绪,而在体验过这些最初的感觉后,我已经完全无动于衷。我近乎一架机械,只用“是”或“不是”回答他的问题。他恼羞成怒:“你可以做得好一点儿! 非要我把你身上的所有事都扒出来吗?”
“那有什么用呢?” 我说。“我要说的话你们已经知道了,它们全写在我签名的那份笔录上。审判已经结束了,我签了判决书,那还有什么用呢?”
“嗯,”他说,“这对我们很有用。严格说来,这不是审讯,我们只是想得到一些补充信息。” 不过,他还是重新从旧的口述开始讲起。显然,所谓的“补充信息”,意思只不过是他们觉得我还在隐瞒着什么。
有时他会改换策略,试图搬出他所有的无神主义论据同我争论宗教。我对争论不感兴趣,我知道他其实也对此毫无兴趣。有一天,我打断了他的论证:"你瞧,我们有信仰的指引。你们有什么?一无所有!”
“哦,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理想。”他说,“我们有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以及坚信的理想。那不是信仰,而是别的东西。”同他争论是徒劳无功的,我对他明说,我觉得他只是在刺激我说话。
我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被传唤去那些不定期的“补充信息”审讯。事实证明,这些审讯和以往一样毫无效果,而且每次都让我更加反感。无论如何,我和审讯者处在完全不信任的氛围之中。谢多夫的事情过后,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另一方面,审讯员也不信任我。事实上,他有几次明确告诉我,我必定向教宗发过某种特殊誓愿,又或许是“告解封印”妨碍我对他畅所欲言 。他说,他从我拒绝合作的态度就能看出这么多。
“太可笑了!”我说,“不过,既然我无法让你相信我的诚意,那就随你怎么想吧。如果你不给我面子,我也不会在乎你的想法!”
有时审讯员会拿来一份名单,上面写着一些枢机主教、主教和普通教士的名字。他会问道:“你知道某某的哪些事?”
“一无所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他。”
“你不是在罗马待过吗?”
“是的,但我从来没见过他。他现在是在罗马吗?”
有一天,当我坐在审讯员的办公室里,他给了我一本书让我读,那是一本带有共产主义者报复意图的教会史,书中写满了有关十五世纪的枢机主教的丑闻。“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他说,“现在,把你所知道的有关这些人的事写出来。”他把枢机主教、主教和普通教士的名单递给我。我拿着名单,写下了自己略有所闻的名字,数量少到几乎跟没有差不多。在我写完后,他把名单撕掉了。“你在干吗,”他问,“想糊弄我?”
还有一次,审讯员用几个小时向我询问有关俄罗斯学院的事以及它的人员情况。许多人的名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而关于那些我认识的人,我把我所知道的事告诉了他:“他是个很好的信徒。他非常热诚。他的俄罗斯历史课教得很好。他的声音很好听。” 审讯员会大发雷霆:“你知道那不是我们想知道的!” “抱歉,但我只知道这一类事情。” 有几次,他向我问及有关谢普提基都主教的事,我坦言自己只见过他两次,并且努力让他相信这一点。我用自己所知的一切得体地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至于其它的事,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并不打算编故事迎合他。
在审讯期间,他会时不时地拿出一个“提案”:万达 · 瓦西列夫斯基(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ий )正在组建一支前往东部前线作战的部队,很多波兰人应征入伍参加了抗德战争。他说,他们需要司铎,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我知道万达是共产党员,我觉得共产党员不会关心随军司铎的事,除非他们是另有所图。“我没兴趣。”我说,“不用了,谢谢。”
“好吧,”他说,“你再考虑一下吧。假如你改变了主意,请记得这个提案仍然有效。”
不过下次他传唤我的时候,提案却起了变化。他没有建议我加入万达的军队,而是提议我加入英国的安德斯军,一支由自由波兰人组成的军队,将在即将开辟的第二战场作战。我摇了摇头:“别和我做交易。”

“安德斯军”(正式名称“自由波兰第二军”)的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1940年1月29日被移送卢比扬卡,后获释参与对德战争
“交易?”他说,“没人说要做什么交易。”
“现在你看看吧,”我说,“我昨天并没有进这个监狱。我被判处了十五年的苦役,你却要取消这个判决把我送到英国去,又或者,你指望我在安德斯军以某种方式服刑。如果你们是因为判决有误才试着讨好我,那就释放我。不然,我根本就不打算陪你们这些人玩什么把戏。”
之后,他总是拿出不同的提案。有一次,他说假如我割断与教宗的关系,就送给我一个俄罗斯堂区。审讯员还说教宗站在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边,他显然是在操弄政治,审讯员还想让我在某天就这个内容发表一个广播演讲。“可笑!”我说。

墨索里尼与教宗庇护十一世
“这两年来,”他说,“你一直在试图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你来俄罗斯只是为了服务信众。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确实是有些机会,却要我付出这样的代价!”
“好吧,我搞不懂你了。”
“你们当然不懂我,”我说道,“很明显,你们从来就不懂我。但我在这里呆得够久了,久到能知道你们在打什么主意。我对任何交易都不感兴趣,我们就当把这些事都忘了吧。”
他不肯放弃。还有一次,他提议让我去罗马安排一个教宗和苏联的协议。我笑了:“谁来给我授权?”
“哦,我们会解决的。”不过首先,他们要我去上无线电课程和电报课程。
“学这个干什么?”
“干什么?从罗马给我们发消息!”
我又笑了,打断了他的话。他时常提起这个话题,但我告诉他,我根本不愿意对此进行讨论。
在整个审讯期间,我只见过谢多夫一回。一天早上,我被押到他的房间,发现他神情紧张,心事重重。他让我回去洗个澡,然后给了我一套干净的衬衫和长裤,让我去和贝利亚面谈。我大吃一惊。但谢多夫比我还着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警告我,不要讲出我先前签字的完整笔录里没有的事情。
于是我洗漱完毕,穿上了谢多夫给我的干净衣服,狱警带我原路返回,先是穿过走廊,上了几层楼,穿过一排前厅,接着把我领到一个装修豪华的大房间里,房间里有厚重的红色门帘和一张巨大的、经过抛光处理的桃花心木办公桌。我们到达的时候,房间里没人。我紧张地等待着,准确地说,是焦急地等待与那位一手遮天的秘密警察头子的会面。门帘拉开了,但进来的不是贝利亚,而是贝利亚的一个助手,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健壮男子,头发花白,面容肃穆,身着剪裁得体的制服。他向我道歉,说贝利亚本人突然被叫去克里姆林宫开会了。
很快,我们的会面就发展到与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了。英国有一位曾是波兰军随军司铎的波兰人主教,他曾带了几位英国专员来俄罗斯视察战争的进程,观察从德国人手中夺回的领土上民众的生活状况。主教回到英国后写了一本书,抑或是一篇文章,他在书中提到有10万波兰人死在了某个苏联劳改营或苏联占领区中。苏联方面否认了他的说法,而且担心这种言论可能会对战时同盟产生影响。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40年4月至5月间在卡廷森林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了有组织的大屠杀,史称“卡廷惨案”
我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贝利亚助手的描述也不够清楚。他更想知道我对这一事件了解多少,我是否能提供相关细节,尤其是有关那位主教的情况。在克里姆林宫看来,这肯定是一个严重的事态,以至于派来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层对我进行审讯,但我无法向他提供任何信息。无论是这个指控还是那个事件,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从未见过那位主教。当那位助手终于相信我对此一无所知,他就将我们的会面时间缩短了。我被带回了牢房,既吃惊又茫然,但我之后再也没有听说任何有关那件事的消息。
到了1943年的春天,由于战争原因,监狱里的伙食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食物状况的话题偶尔会以极不愉快的形式出现在我与审讯员的谈话中。他会提醒我,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前线死去,百万之众的人口正在家里挨饿。接着,他在结束自己的短篇独白时补充道:“我们对你过于宽大了,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而你,一个与人民为敌的人,却在监狱里悠闲地生活,吃饱穿暖,既不做任何事情帮助我们,也不为自己所受的待遇心怀感恩。”末了,我被叫去签了最后一份文件,以证明我的审讯已经结束,他难以置信地对着我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搞不懂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