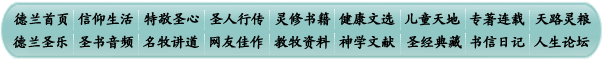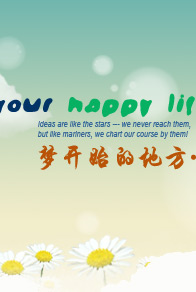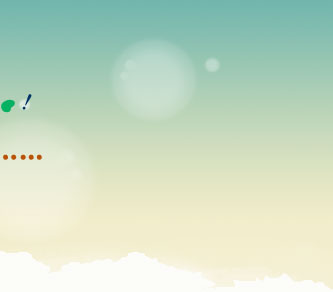耶稣带着门徒们离开拉玛,朝靠近息哈尔的塔纳特-西罗走去。那时夕阳低垂,仿佛也知道祂即将走上苦难的道路。因为法利塞人都去了耶路撒冷过节,塔纳特淳朴的百姓满心欢喜地迎接耶稣,就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他们不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到祂温暖的笑容。
村里留下的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卧病在床的患者、眼中带着忧虑的妇女和天真无邪的孩童,还有几位守着羊群、默默望着夕阳的老牧人。在拉玛和塔纳特,我看见人们成群走过金色的麦田,细心捆起沉甸甸的麦穗,用长竿抬回家和会堂。那景象美得像一幅画,却让我心头泛起说不出的哀伤——因为耶稣正望着这一切,仿佛是在告别。
祂停在田边,也在投宿的塔纳特-西罗向众人讲话。祂的声音比往常更低沉,话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预兆,像是在暗示自己生命之路即将走到尽头。祂仍温柔地召唤每一个人近前,轻声说:“来吧,到我跟前来,你们的灵魂将得安慰。你们要记住:天主最喜悦的祭献,不是外在的礼仪,而是一颗痛悔和谦卑的心。”
之后,耶稣转身向北,朝着靠近默洛兹山的阿塔洛特走去——那里,祂曾应人们的哀求,让一个死人复活。一路走了四个时辰,抵达时已近黄昏。
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拄着拐杖颤抖的老人、被搀扶着的病人、紧抱婴孩的母亲,还有那些常年躲在人后、惧怕法利塞人的穷苦人。他们眼中含泪,向祂伸出双手,渴望最后的安慰与治愈。那一刻,谁都能感受到——祂的时间不多了。
阿塔洛特的法利塞人与撒杜塞人对耶稣充满怨恨,曾因惧怕祂而紧锁城门。但这一次,祂的声音既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又浸透着深切的怜悯。祂明确提醒这些单纯的人小心法利塞人的虚伪,也毫不避讳地谈到自己的使命、天父的旨意、即将来临的迫害与死亡,并谈及复活、审判,以及背起十字架的意义。
那一天,夕阳西下时,祂的手抚过许多苦痛的身躯:瘸腿的重新站立,失明的再见光明,患水肿的渐渐舒缓,生病的孩子绽出笑容,长期血漏的妇女也终于得着了洁净。
门徒们特意为经师在阿塔洛特城外安排了安静的住处,就在一位淳朴的老教师家旁边。那位老人独自住在开满鲜花的小院里,显得格外安宁。耶稣和门徒们洗去脚上的尘土,简单吃了些食物,就一起前往阿塔洛特的会堂度过安息日。
会堂里早已坐满了人,不仅有从四周村庄赶来的,还有许多曾亲身经历耶稣医治的人。主持礼仪的是位年长的法利塞人——他腿脚不便,这次没去耶路撒冷。他虽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大家却暗地里觉得他装模作样,有几分可笑。那天的经文诵读了关于分娩所致的不洁、癞病的条例,也提到了厄里叟曾以初熟的粮食使新麦增多、以及纳阿曼癞病获得洁净的往事……
耶稣讲了很久的道,随后转身走向妇女站立的角落,叫一位可怜又驼背的寡妇上前来。这些年来,都是她的女儿们搀扶她进出会堂,让她坐在那个熟悉的角落。她已经病了整整十八年,却从未开口求过医治——她的腰背弯曲得厉害,走路时上身几乎贴到地面,仿佛要靠双手支撑。
正当女儿们扶着她慢慢走向耶稣时,耶稣温和而坚定地说:“妇人,你从疾病中得释放吧!”同时伸手轻轻放在她佝偻的背上。
刹那间,她就像一棵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一下子挺直了腰身!她立刻高声赞美:“愿以色列的天主永受称颂!”接着就伏倒在耶稣脚前,感激的泪水潸然而下。全会堂的人看见这景象,也都欢喜不已,同声颂扬天主。
只有那个身体扭曲的老法利塞人,心中又妒又怒——这样大的奇迹,竟发生在他主持的会堂!他不敢直接顶撞耶稣,就转身对着众人,端起一副严厉的架子斥责说:“一星期有六天可以工作,要治病,六日内不来,偏等到安息日?”
那法利塞人仍不死心,高声叫嚷:“要治病,为什么偏要选在安息日?那六天难道不行吗!”耶稣转身直视着他:“虚伪的人哪!你们当中,有谁在安息日不解开槽边的牛或驴,牵去饮水?而这女人——她是亚巴郎的女儿啊!被恶魔束缚了整整十八年,难道不更应在安息日这天解开她的锁链吗?”
那跛脚的法利塞人和他的同党顿时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而围观的群众却因这显而易见的奇迹雀跃不已,纷纷高声赞美天主。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那刚被治愈的妇人的儿女和几位年轻亲人——他们簇拥在她身旁,泪水与笑容交织,激动得说不出话。是的,全城的人都为她欣喜,因为她本是城中一位广受爱戴、乐善好施的女子。而那个跛脚的法利塞人,自己明明也急需医治,却只因这虔诚的妇人得痊愈而妒火中烧——那神情既可笑,又透着一丝可悲。
耶稣继续向众人阐释安息日的真谛,语气就如当初在圣殿中治好贝特匝达病人、面对质疑时一样坚定不移。当晚,祂仍然借宿在阿塔洛特城外那位老教师的简朴家中。第二天,祂还特地前去探望得痊愈的妇人——她一向慷慨仁慈,那一日更是大开筵席,周济了许多贫苦之人。
安息日结束后,耶稣在会堂行了辞别礼,又继续前行约两个时辰,最终在基宁附近的一家客店落脚歇息。
次日清晨,祂带着门徒向北跋涉约八个时辰,一路穿过厄斯德隆青翠的山谷,踏过清澈的基雄溪水,终于抵达哈达德黎孟。途中,他们右侧掠过了厄恩多尔、依次勒耳和纳因三地。黎孟城离玛革多至多不过一个时辰的路程,离依次勒耳与纳因也相距不远;向东距大博尔山约三个时辰,向西南到纳匝肋也大致相当。这是一座繁华兴旺的城邑,因为有一条贯通提庇黎雅与海岸的军商要道正从这里经过。
耶稣在城门外一家客店暂住。祂一路行走,一路宣讲,途中还医治了许多牧羊人与困苦中的病人。祂不断强调“爱你的近人”这一诫命,叮嘱众人不仅要爱撒玛黎雅人,更要爱每一个人。也正是在这段旅程中,祂亲自讲述了那位慈善的撒玛黎雅人的比喻。
在哈达德黎孟,耶稣向众人宣讲死人复活与末日审判的道理,并医治了许多病患。大批群众前来听道——他们曾到耶路撒冷寻找耶稣,却在他离开后的第二天才抵达。与此同时,宗徒和门徒们在周围的村镇继续传扬福音。
就在耶稣离开耶路撒冷的第二天,比拉多突然颁布禁令,以死罪威胁禁止加里肋亚的热忱派离开圣城——尽管他们早已归心似箭。许多人被扣作人质,关押起来。然而不久后,比拉多却出人意料地释放了这些人,并准许他们前往圣殿献祭,之后便可离城。近午时分,他自己也动身前往凯撒勒雅。
这些一度被囚的加里肋亚人又惊又喜,急忙赶往圣殿献上赎罪祭,因为他们自觉礼仪上沾染了不洁,尚未完成当行的祭献。
这一日,正是人们照惯例携礼物来圣殿的日子。有人买了祭牲前来献祭,更多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群——则变卖多余之物,将所得投入专门的献仪箱中。富足的人往往出资帮助贫弱的邻舍,使他们也能完成献仪。我看见殿内设有三个不同的献仪箱,每处都有人指导规矩;有些朝圣者正专心祈祷,另一些人则在宰牲场忙碌地预备祭物。
圣殿内人虽不少,却并不拥挤。四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以色列人:有的躬身敬拜,有的肃立默想,还有的全身伏于地上,身披祈祷巾,虔诚祈祷。
祈祷声未落,噩耗已传来
我垂首从圣殿一侧的骇人高处向下望去,狭窄的街道上尽是疯狂奔走的妇女与孩童,他们挨家挨户哭喊着传递噩耗——许多住在圣殿周边的小贩和苦力,在方才的混乱中惨遭屠戮。圣殿内的景象凄厉可怖,人们从每一个能逃生的缝隙中拼命向外奔涌。长老、管事、持械者、法利塞人……无一不惊慌失措地向外逃窜。
四处是倒卧的尸身、凝固的鲜血和散落的银钱,受伤者与垂死之人横陈于地,在血泊中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不久,那些在耶路撒冷有亲人意外罹难的家属纷纷赶来,哀哭声、愤怒的呼喊、痛苦与绝望的咆哮此起彼伏,交织成一片凄惨的合唱。法利塞人和司祭长们惊惶万状——圣殿竟遭逢如此可怖的亵渎。因惧怕被尸体玷污,司祭们不敢再踏入圣殿半步,庆典就这样在血色中戛然而止。
我望着那些耶路撒冷居民的遗骸,被痛哭的亲人以殓布缓缓包裹,置于尸架上抬离;其他死者的躯体则由奴仆们默默运走。所有遗落的物件——牛羊、食物、各类物品——都不得不弃置于圣殿之中,因一切皆已成为不洁。除了守卫与工人,所有人皆仓皇离去。
此次死亡之数,甚至超过了先前修建水渠时倒塌事故中的亡魂。除了无辜的耶路撒冷居民,罹难者大多属于高卢人犹达的追随者——他们曾激烈反对帝国税与水渠捐,坚信这些征收亵渎了圣殿的特权。也正是这批人,当初曾大胆抨击比拉多的提议,并在之前的冲突中手刃数名罗马士兵。比拉多趁他们手无寸铁之际发动袭击,既为死去的士卒复仇,也算是对黑落德恶意拆毁塔楼一事的残忍报复。
死者之中,还有众多人是来自提庇黎雅、高隆、上加里肋亚与斐理伯的凯撒勒雅。
注:
相关记载可参看《肋未纪》第12-14章及《列王纪下》4:42-5:19中关于洁净与不洁的条例,以及厄里叟先知以二十个麦饼饱饫百人的奇迹和纳阿曼患癞病得治愈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