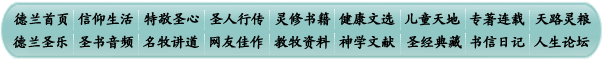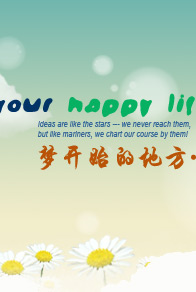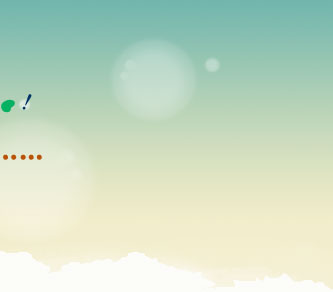巴尔纳伯的父亲住在城西的乡间,零零散散的房子点缀在缓坡与田野之间,基提翁就静静地坐落在当中。有些人家挨得近,自然地聚成小村落,也有些独门独户,守着自家的果园和菜地。他家的屋子挺好看,一侧顺着地势修成了阶梯的样子,深褐色的木墙像是刷过桐油,在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也不知是人工做的,还是岁月久了自然形成的颜色。台地上种了花草与小树,长得郁郁葱葱。除了阶梯之外,房屋四周还环绕着柱廊和敞开的长廊,廊边树影摇曳,十分清爽。
再往外去,是一片蔓延开的葡萄园,旁边空地上整齐地堆着木料,里面夹着好几根特别粗的原木,还有些雕成人形的木雕像,并不显得乱,反而留出了可以走的小路。看样子这些材料是用来造船的。我曾看见几辆长长的货车,宽度刚好能装下木材,装着沉重的铁轮,由几对牛慢吞吞地拉着,牛与牛之间隔得很远。不远处,就是基提翁靠着的那片森林,高大、宁静,在林风吹拂下显得特别美。
巴尔纳伯的父亲是一位鳏夫,他的妹妹带着女仆住在附近,帮忙料理家务、准备饭菜。那时还是安息日,所以跟随耶稣的外邦人和从撒拉米来的哲学家没有上桌一起吃饭,而是在敞开的长廊里边走边吃,手里拿着食物,站在廊柱下听耶稣讲话。餐食中有禽肉、扁平的鱼、饼、蜂蜜和各种水果,还有用香草卷起来的肉卷,各式各样的菜,摆满了一桌子,香气扑鼻。耶稣谈到了祭献、天主的恩许,也慢慢讲起先知的使命。
正吃饭的时候,来了几群四五岁左右的穷孩子,衣衫褴褛,挽着小编织篮,拿出能吃的香草想换点饼或别的食物。他们特别喜欢凑到耶稣和门徒坐的那一边。耶稣站起身,把他们篮中的香草轻轻拿起来,再把桌上的食物给他们装满,又伸手祝福了这些孩子。那一刻,温暖洋溢,格外感人。
第二天清早,耶稣在巴尔纳伯家后面一片微微隆起的高地上教导众人,那地方设有讲席。从房屋到讲席,先得穿过一排宏大的葡萄架,藤叶交错,浓荫像走廊一样。来了许多听讲的人:耶稣先对矿工和其他劳动者讲话,再对外邦人,最后也对那些与异族通婚的犹太人。很多患病的外邦人求耶稣医治,也请求准许他们听道——大多是走不了路的人,被安置在讲席旁的床榻上。耶稣对劳苦的工人们讲道时,用《天主经》和炼金之火的比喻,说人心也必须在考验中炼净,就像火里炼金;对外邦人,祂则用野葡萄枝作比喻——枝条如果不修剪,就结不出好果子。祂讲述独一的真神如何像一家之主,对待子女和仆人虽有区别,却同样赐下恩宠;又说明外邦人蒙召,就像野枝被接到真葡萄树上,从此能得到生命的滋养。后来谈到混合婚姻,他说这样的婚姻虽然可以宽容,但不能轻易认可,除非有一方可能归化或成圣,且绝不能出于私欲,双方都该有圣善的意愿。祂对此并不表示赞成,反而多次提醒其中的困难,并赞美那些能在主内养育纯洁子女的人是有福的。他也提到犹太丈夫或妻子不能因为婚姻就放弃自己的信仰,相反,他们应该是家庭中信仰的支柱。并谈到虔诚养育儿女的责任、恩宠来临时要回应,以及补赎和圣洗的重要。
之后,耶稣治好了病人,和巴尔纳伯一同吃了晚饭。在朋友陪伴下,祂又往城对面远处分布的几处蜂场走去,周围是大片的花园。附近有泉水和小湖,耶稣就在那儿继续讲比喻、教导人,之后大家才进城进入会堂,把关于祭献与恩许的话题讲完。
那时,有几个博学的犹太人在那一带巡行,用各种狡猾的问题试探耶稣,但都被祂平静地化解了。他们似乎不怀好意,问题涉及混合婚姻、梅瑟处死民众的事、亚郎造金牛犊和后来受罚等等。
第二天好像是犹太人的庆节或守斋日,会堂举行了早祷和讲道。礼仪结束后,耶稣带着门徒和几个外邦青年由北门离城,一些犹太经师和勒加布人也跟着一起走,总共有百来人。他们走了大约一小时,来到养蜂的地方,只见东边远处排列着一人高的白色蜂箱——像是用芦苇或树皮编的,一层一层,满是小孔。每一处蜂箱前都开辟了一片香脂木田,正值花期,花开得绚烂。每块花田四周都细心围了篱笆,远远望去,这些错落有致的小花圃连成一片,竟像一座微缩的城郭,静谧而庄严。这一带的外邦风情特别明显:壁龛之中立着造型奇特的玩偶,它们的尾巴像鱼鳍一样弯弯翘起指向天空,手臂与腿脚都很短拙,面容介于人和非人之间,仿佛正用沉默的姿态,诉说着远方国度的信仰与古老传说。
这个小村落里住着不少养蜂人,他们的屋舍朴素实用,里面存放着各种蜂箱、刮刀、滤网,还有熏烟用的工具。客栈算是这里最气派的建筑了,带着好几间附属棚屋,围出一个大院子。院中棚廊交错,摆放着成排的支架和长垫,供人休息。管家是个外邦人,周到地打理一切,照顾雇工们的生活。犹太人有自己专用的厅堂和祈祷处,和他们分开。蜂蜡和蜂蜜的加工就在屋里和长棚下进行——这儿真像个热闹的集散地。
我还注意到许多开黄色小花的小树,叶子泛着淡黄色,不是深绿。落花积了厚厚一层,像软毯子铺满地面。树下铺开长垫,工人们正仔细挤压这些花瓣,提取染料。小树先是种在盆里,之后常常连土带根被移种到石缝里。这样的树种,在犹地亚也能见到。这一带还种了大片的亚麻,人们从中抽取长长的丝线,准备织成细布。
从基提翁往北走大约半小时,一道清泉从岩洞里涌出来,先穿过城区,再流经耶稣走过的野地。有些段落水流很急,有些则架了木桥——撒拉米的水渠大概就从这里发源。泉水汇成一个小湖,将来要在这里为人施洗;耶稣的话里也隐约提到了这件事。这一带野花开得灿烂,沿途种满了橘树、无花果树、醋栗丛和葡萄藤,充满生机。
耶稣来这儿,主要是为能不受打扰地教导外邦人。整整一天,祂就在客栈的花园和凉亭间讲道,众人有的站有的坐在草地上,安静聆听祂讲解《天主经》和真福八端。面对外邦听众,祂直接指出他们众神的虚假和来源的卑下,又讲到亚巴郎怎样蒙召、怎样离开拜偶像的本族,以及天主一路怎样引导以色列。祂的话语清晰有力,在场聆听的大约有一百人。讲道结束后,众人在客栈用餐,外邦人另外坐一桌。食物有面包、长条的山羊奶酪、蜂蜜和当季水果。客栈主人虽是外邦人,却举止谦逊、含蓄有礼。当晚外邦人散去之后,耶稣继续教导犹太人,带他们一起祈祷,众人就在客栈过夜。
基提翁比撒拉米更热闹、更兴旺——撒拉米只有港口和一两条街有买卖,这里却充满活力。耶稣进城的那一侧有个大市集,卖牲畜和禽鸟;市中心还有一处漂亮的市场,高耸的建筑内外挂满了各种布料和彩帘。城的对面几乎全是金属工匠的铺子和铸坊,敲打声不停——不过大多数工场其实设在城外。他们打造各种器皿,尤其是一种轻巧的大椭圆烤炉,带小盖子和顶侧双把手。制作时先把金属弯出形状,再放进巨炉中,用长管把熔化的金属吹成中空的容器,外黄内白,用来装水果、蜂蜜或糖浆出口。海运时这些容器架在支架上,若走陆路,就用杆子穿过把手抬着走。
第二天,耶稣再次在蜂场教导众人,听道的人增加到几百个。祂用很有说服力的话向外邦人指出他们信仰的错误,揭露他们的众神如此卑微,竟还要靠各种牵强的说法来自圆其说。祂劝他们放下诡辩和空想,不再维护虚假,以单纯的心专注仰望天主和他的启示。有些手拄行杖、像游学士一样来的外邦人听到这里,生气地离开了,一路抱怨不停。耶稣看着他们的背影,说道:“随他们去吧!这总比留下来,把听见的道理又编成新的偶像要好。”祂预言这片美丽的土地将来一定会荒凉,城邑与庙宇将被毁灭,审判必要临到列国。祂指出,当偶像崇拜到了极点,外邦的信仰终会消失;祂也详细说了对犹太人的惩罚和耶路撒冷的毁灭。外邦人反而比犹太人更容易接受这些话——后者常常倚仗恩许而提出反对。耶稣就与他们一起查考先知书,解释关于默西亚的段落,指出应验的时刻已经近了:默西亚要在犹太人中兴起,却被自己人否认;他们要嘲笑祂,当祂申明自己就是所盼望的那一位时,反而要捉拿祂、处死祂。许多听众脸上露出不高兴,耶稣就提醒他们历来是怎样对待先知的,并最后说道:你们既然这样对待预报者,也必这样对待被预报的那一位。
勒加布人与耶稣谈起玛拉基亚时,语气非常敬重。他们说,他们将玛拉基亚看作天主的天神,说他小时候就曾出现在一些虔诚的人家里,常常神秘地消失,至今也没有人确知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去世。他们详细讲了他关于默西亚和新祭献的预言,耶稣便温和地向他们解释,这些预言正在这时候、在不久的将来,一一应验。
离开蜂场后,耶稣与一大群人同行——一路上不断有人离开,走了好几个钟头,才回到巴尔纳伯的家。同行的人里,很多是犹太社团的年轻人,正要上耶路撒冷过五旬节。就算这样,留在耶稣身边的,还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三十几位外邦妇女和少女,还有十来个犹太女孩,早已聚在花园入口迎接耶稣。她们吹起长笛、唱着赞美诗,头戴花冠,又把绿枝铺在祂要经过的路上。她们还特地放好了垫子,向祂深深鞠躬,献上花环、香草和小瓶的香水。耶稣感谢她们,也对她们讲了几句温暖的话。她们跟着祂走进巴尔纳伯家的院子,把礼物摆在聚会厅里,又用鲜花与花环把各处都装饰起来。这场迎接和等候虽然简朴安静,却隐隐透出和圣枝主日相似的气息。天色渐晚,众人不久就各自回家了。
外邦妇女的衣饰令人眼花缭乱。少女们戴的帽子样式别致,就像我小时候用芦苇编的“布谷鸟篮”。有些很朴素,有些绕着小花环,垂下无数流苏坠子,轻轻拂过额头。帽檐总是用绒线或羽毛扎成花环的样子。面纱戴在帽子底下,分成两片,可以在前面敞开,也可以掀到帽后——那样面纱就会垂到脖子边。她们束腰束得很紧,胸前戴着饰品,颈间系着各种丝带和珠串。裙子特别宽大,由好几层薄料叠穿,每层比外面那层长约一拃(差不多九英寸),最外那层最长。手臂并没有完全遮住,衣服没有袖子,只有长长的垂片,她们还在臂上系着小花环。衣裳颜色鲜艳:黄的、红的、白的、蓝的,有的带条纹,有的绣着花。头发像面纱一样披在肩上,发尾用流苏绳扎起来,免得被风吹乱。她们赤脚穿着凉鞋,鞋尖俏皮地往上翘,用细带固定。已婚妇女的头饰没有少女那么高,额前有硬叶片遮盖,尖端垂到鼻梁,再弯过耳朵上面,露出戴珍珠耳环的双耳。头饰本身是镂空的,编进了发辫、珍珠和各种饰品。她们还披着长斗篷,松松地垂在背后。随行的孩子们只用布带遮身,布带过肩在胸前交叉,系在腰间,盖住身体中间。这些妇女为等候耶稣,已整整等了三个时辰。
巴尔纳伯家早就准备好了饭菜,但宾客并没有斜躺着吃。食物是放在小木板上递给每个人的,就像船上用的那种木托盘。许多长者聚在这里,也包括耶稣在会堂治愈的那位老经师。巴尔纳伯的父亲是位敦实方正的老者,一看就知是做惯了木工的人。那时候的人,看上去比现在的人要强壮得多。
之后,我看见耶稣坐在基提翁城外泉水边的讲席上,为新皈依的人行洗礼做准备——门徒先给犹太人施洗,再给外邦人施洗。
耶稣也在这里与犹太经师讨论割损礼的问题。祂说,不应该强迫皈依的外邦人行割损,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同时,犹太人也不该允许这些皈依者进会堂,以免引起别人反感,却应当感谢天主使外邦人放弃偶像、等待救恩。可以要求他们实行其他的克己,比如心的割损,并克制贪欲。耶稣安排他们和犹太人分开接受教导和敬礼,既保持虔诚,也彼此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