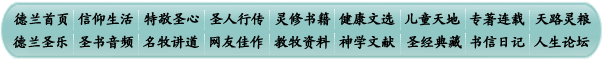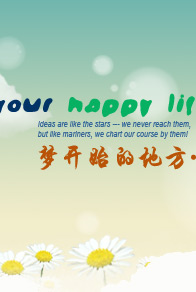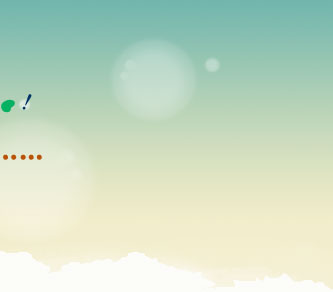现代洗礼神学倾向于将此圣事的重点从客观的恩宠礼物转移到主观的自由行使上,认为圣事的拯救力量主要在于受洗者对信仰恩赐的意识。因此,关于婴儿洗礼的争论再次兴起,有些人认为婴儿洗礼缺乏洗礼圣事的基本要素,因为它不涉及婴儿有意识的参与。
我们不应忘记,教会一直要求儿童接受洗礼有一定的主观同意因素;这体现在那些为儿童洗礼的成人的信仰和愿望上。所涉及的信仰是教会的信仰,由他人持有,而不是由儿童持有,因为儿童对此并无意识;尽管如此,这也还是儿童自己的信仰,因为儿童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其家庭的成员,而家庭又是教会的一部分3,在教会中,所有成员都因圣神而充满活力并团结在一起4。
在洗礼圣事中,就像其他圣事一样,也有一个客观因素,它超越接受者当前的道德状况,它产生的影响独立于受洗者的主观倾向,并引导受洗者走向圣洁5。洗礼的主要作用是实现耶肋米亚先知书中著名的预言6,该预言宣告了旧以色列的圣事和新以色列的圣事之间的差异,宣告之前的圣事是物质的,没有果效的,宣告之后的圣事是属灵的,有果效的,因为以色列将律法写在人们的心里。
圣保禄宗徒所说的这种性格的植入是在灵魂的本质和运作中实现的,尽管不同的学派对它有不同的解释;它的基本特征是它是超性的,它通过赋予那些接受它的人在基督里的新生而将他们标记出来。这种重生发生在婴儿身上,婴儿没有任何意识、意愿或行为,对自己所接受的一切仍然毫无知觉,尽管这种恩赐旨在给重生者带来巨大的变化并灌输新的倾向。显然,天主教对洗礼圣事的这一看法与主观主义截然相反,主观主义强调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鄙视任何非个人行为所产生的东西7。
在天主教看来,超性的美德是通过洗礼圣事被赐予灵魂的,显然不是在行为上,而是作为一种习惯,这样,在一个基督徒的灵性成长过程中,他就能够自由而有意识地履行超性美德的行为。显然,今天所谓的意识化,即把人简化为自我意识和感官体验,与天主教神学根本不相容; 因为它们不是心理的经验,也因为它们不涉及梵二后大公会议人类学所定位的那些体现人的全部价值的个人行为,所以新神学不能接受洗礼圣事的恩宠给灵魂带来变化的现实,洗礼圣事使灵魂超越其自然水平之上,并引导灵魂走向由超性活动组成的生活。
正是由于拒绝了人依赖天主的原始观念,才必然导致教会以婴儿洗礼无需人的有意识行动为由,要求取消婴儿洗礼,代之以不受这种反对意见影响的成人洗礼。由于洗礼圣事的恩宠与接受洗礼圣事的个人无关,因此在一个一切都取决于主观体验至上的体系中,婴儿洗礼是不存在的。
我不想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在结束对洗礼圣事的讨论之前,我不能不指出,在这里,神学观点也是哲学观点的产物:否认潜能和行为理论必然导致否认受洗的婴儿在潜能中拥有美德,这种美德在适当的时候会随着他的成长而产生。在新的观点中,注入的、看不见的信仰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对天主创造不可见之物和可见之物这一事实的否定的必然结果:“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8”。
备注:
3. 这与旧约中通过割礼接纳婴儿加入天主的子民有相似之处。[译者注]。
4. 在卡洛林时代(即九世纪),这种主观因素非常强烈,以至于在洗礼前的训示、检查和整个准备仪式中,沉睡中的婴儿都与父母一起在场。
5. 即使受洗的成人处于重罪状态,这种效果也是存在的。见加斯帕里,《教理问答》,第 197 页。
6. 《耶肋米亚》,31:33我愿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的断语──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作他们的天主,他们要作我的人民。
7. 《法国儿童洗礼宣言》(Déclaration des évéques de France sur le baptéme des enfants)充满了这种主观主义精神:婴儿洗礼被视为可能被抛弃的传统;该文件建议逐步开始领受复活基督的奥秘,包括推迟洗礼。中世纪的卡萨里派也反对婴儿洗礼,他们认为有意识的行为才是救赎的必要条件。参见《Esprit et Vie》,1966 年,第 503 页。
8. 参阅《尼西亚信经》。“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