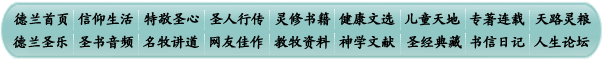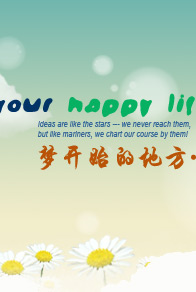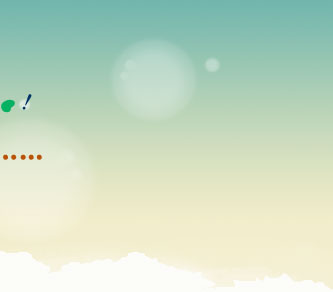虽然托马斯主义在梵二会议上失去了其在哲学研究中的特权地位,但它确实在神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信仰的奥秘应在神学思辨中得到阐释和整合,“以圣托马斯为师15”。
尽管如此,从梵二会议从未引用良十三世 1879 年的《永恒之父》通谕(Aeterni Patris)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梵二会议确实是非托马斯主义的。该通谕赞扬了圣托马斯的教义,赋予其特殊地位,并命令天主教教学机构将其作为标准教义来教授。在若望-保禄二世的宗徒宪章《基督信仰的智慧》(Sapientia Christiana)中,这一惊人的遗漏再次出现,该宪章为管理天主教大学制定了新规则。它详细阐述了神学研究的自由,但对教义的统一毫不关心,却对教学中的多元化给予了极大的宽容。
《司铎之培养法令》中对圣托马斯的提及被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多元化,这意味着教会研究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至于大学的新规定,《基督信仰的智慧16》规定,天主教大学的入学要求是“具备该国世俗大学要求的入学资格”。这样做的结果是,要想进入那些通常培养神职人员的天主教大学,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或存在主义哲学的熏陶;这还意味着,教会在自己的研究课程的内容和方法方面的独创性和自由,曾被十九世纪的主教们极力捍卫这种独创性和自由,主要用于反对专制国家的干涉,现在将被抛弃,转而用这种独创性和自由去支持那些无视或否认天主教原则的世俗文化。
教会在《司铎之培养法令》 “学习计划17”中所作的这些改变,既抛弃了托马斯主义,也抛弃了古典主义,转而采用融合多元主义,这是普遍丧失本质的又一例证,也是将一种实体与另一种实体区分开来的界限消失的例子,从而使两者都能保留其具体特征的又一例证。梵二后教会的一切典型特征,在逻辑上都可以从这个本质丧失的核心问题中推导出来。哲学和神学不再被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而是被教授为一个混乱的整体,可以用不同方式表达的,而不必担忧所教授的内容是连贯的还是不连贯的,是一致的还是自相矛盾的。
《永恒之父》通谕(Aeterni Patris)将托马斯主义置于优先地位的理由如下。首先: 托马斯主义基于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信念,反对部分和完全的怀疑论:理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那些自然可知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是启示真理所预设的。第二:基于精神掌握一切真理的能力,托马斯主义阐明了信仰的真理,只要这些真理能够通过与自然真理的类比来理解。第三:在这样证明了某些自然真理,并阐明了已揭示的真理之后,托马斯主义继续捍卫这些真理的有效性,以对抗反对意见。所有这三个理由都可以归结为承认自然秩序与超自然秩序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承认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区别,而所有天主教的思辨思想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梵二实际上取消了托马斯主义的特权地位,因为它对《永恒之父》通谕(Aeterni Patris)只字不提,将托马斯主义视为一种方法而非真理体系,鼓励与现代哲学接触,但却没有说明这种接触的目的是什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18,现代化思想流派往往在口头上承认它在实践中否认的东西;而且由于历史学和心理学事实表明,某些好的东西在实践中受到的破坏越多,人们对它的口头赞美就越多。因此,1979年在《永恒之父》通谕(Aeterni Patris)颁布一百周年之际,在罗马举行的圣托马斯会议承认了已经发生的变化:“梵二会议尽管提到了圣托马斯,但我们现在所处的神学多元化时期已经开启19”。
备注:
15. Optatam Totius,16。“以圣托马斯为师"。
16. Sapientia Christiana,32。
17. “课程计划”。
18. 见第 49 和 50 段。
19. Atti of the conference, 罗马 1981, p.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