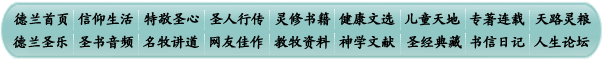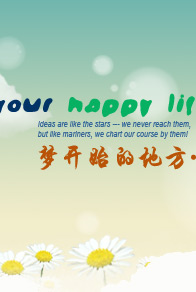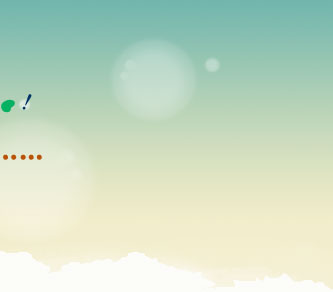尽管在梵二会议的文本中并没有白纸黑字地记载下来,关于这个思想的改变,且它一直受到传统派更积极的支持者的抨击,其中最主要的是费利奇枢机主教Cardinal Felici,但它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教会中的普遍观点。大公会议本身确实指出,在教会的新发展中,“婚姻的精神性1”正不断地被重新表述,现代社会的变化“正以各种方式更加清楚地2体现出婚姻的真正特征”。显然,大公会议无意否认,天主教体系中婚姻一直自有的精神性。那么,所谈论的其实是一种新精神性。伴随着这一变化的是惯用的委婉说法3,即赞扬现代社会为婚姻和家庭提供的各种帮助。似乎没什么能让大公会议的诸位神长的眼睛得以拨云见日:无论是所有昔日基督教国家都允许离婚,还是试婚现已成为普遍现象,抑或是避孕已成为合法甚至是强制性的,甚至是堕胎的普遍合法化,尽管所有这些现象都为梵二大会知悉并公开谴责。
背离传统教义并不影响基督徒婚姻的超性层面,因为它体现和表达了基督与教会的结合。它影响的是婚姻作为一种自然制度的结合性和生育性方面。
两性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差异表明,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完全有机体互补性是为了促成两个生命体的结合,使他们成为《圣经》中所言“二人成为一体”;在康帕内拉Campanella生动的比喻中,有机体互补性就像一只手套与另一只内部翻出的手套相契合。这种结合进一步又是为了两个人的道德结合而安排的,他们虽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生命体,但通过这肉身结合尽可能地实现了充分的共融。事实上,婚姻结合是两个不同性别的理性受造物所能进入的最完满的结合。
然而,完美的个人结合实际上并非经由肉身结合而真正实现。矛盾的是,就肉体结合本身及其最强烈的状态来看,肉体结合就是两个人分离的时刻,因为在那一时刻,对自己和对方的意识都消失了。完美的个人结合更属于一种伦理秩序,而非肉体秩序,它存在于朋友之间的爱的领域,在这种爱中,双方都不渴求对方,但在更高的层次上,渴求对方并与对方的完美幸福4。
肉体结合的自然结果是生育,而生育无疑是婚姻关系的本质目的;二人相爱,他们的天性产生了第三个人。从天主教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天性就是圣言所发出的理念,并被赋予了真实存在。因此,天性成为道德行为的标准,因为人的道德功能体现在“接受自己的天性、遵循天性内在的法则和实现其目的”。。
因此,有两种驱动力促使人类走向婚姻。第一个是人们寻求在另一个人身上再生自己的自然本能,在这后代身上,他们感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存在,并借此似乎可以逃脱死亡的全部力量。第二个本能是通过将自己作为爱的礼物献给他人来实现自我的愿望。前者可以被称为婚姻的自然美善,后者可以被称为婚姻的伦理美善,但要始终牢记,如果本着正确的精神接受自然美善,自然美善本身就会成为道德美善。
备注:
1. 《大公主义法令》( Unitatis Redintegratio),6。
2. “saepe saepius ”的意思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许多译本中的 “十分”。
3. 《喜悦与希望》( Gaudium et Spes), 47。
4. 若望保禄二世在一九八○年冬季星期三的普众听证会上就《创世记》前几章作教导时说,渴求配偶是一种失调,这似乎就是他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