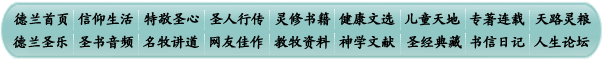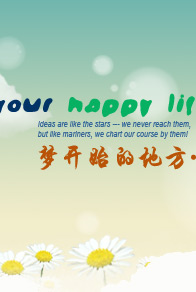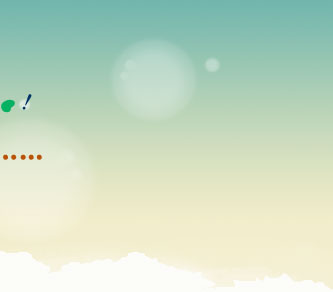斯塔比亚海堡Castellammare di Stabia 的主教写道,“在传教背景下,普世运动的地位与传统上赋予它的地位不同57”。普世运动与传教活动没有真正的关系,因为它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必要派人去传教;每个宗教只需彰显其内在的潜在基督即可。据说,对基督的无意识渴求驱使非基督教宗教彰显其基督教内容,通过追随这种渴求,每个人都能获得救赎。
古典神学以各种方式解决了不信者的救赎问题;通过给予他们特殊超自然帮助的理论,或通过自然幸福状态的理念,类似于未受洗礼的婴儿在理智年龄前死亡的状态,那些通常按照自然美德生活的人可以达到这种状态。但天主教神学家从未教导过,没有天主的恩宠,灵魂就不可能获得永恒的救赎,即超自然的回报。天主的恩宠使灵魂超越自身,与人的自然状态完全脱节。人们如此坚定地认为,自然不可能产生超越自身目标的行为,以至于神学家们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认为人性有两种最终结局,一种是自然而然可以达到的状态,另一种是只有在超自然的帮助下才能达到的状态。但无论采用何种理论,人们始终认为救赎涉及心灵的启迪;潜意识的心灵在实现人类救赎的过程中从未被赋予任何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关于潜意识欲望的理论否认宗教行为发生在理智和意志层面,而是将宗教行为置于心灵晦暗的深处。这样,救赎的问题就被排除在人类道德的范围之外,道德选择涉及到知识、深思熟虑和自由。
但是,认为人的永恒命运是由模糊的本能所产生的非自愿行为所决定的,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如果不行使自已的自由,人就无法得救。新神学家采用这些关于无意识欲望的理论,就更加奇特和自相矛盾了,因为他们普遍强调自我实现或自我决定的重要性。或者说,自我决定归根结底是人的无意识思维的行为?某些心理学流派的影响严重影响了天主教的救赎教义,并产生一种无意识欲望的伪概念,也就是一种没有意志行为的意愿,这种行为既没有功德也没有回报。
备注:
57. O.R.,1981 年 5 月 2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