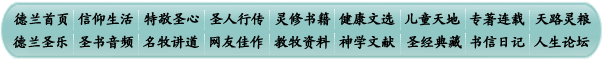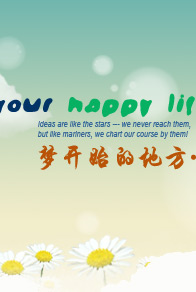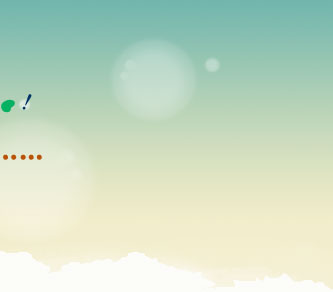以前,个人皈依被视为重要的事情;人们认为,通过等级制度的谈判,而大规模发生精神上的悔改被认为是不合情理的。大规模皈依发生在统治者决定整个社会行动进程,并因此可以规定社会应该信奉什么宗教的时代。野蛮民族的基督教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酋长们皈依基督教的结果,酋长们随后开始协助向其民族传播福音。直到十八世纪,传教活动通常采取影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形式,而不是直接向普通民众传教。在宗教改革时期,整个国家背叛教会的事实,这往往是由于一个统治者放弃了信仰。萨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 of Saxony和英国的亨利八世就是统治者在促成宗教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例子,因为在他们的案例中,整个国家都在其王子的煽动下与罗马决裂。
尽管今天人们一直在谈论宗教自由,但人们所设想的普世合一,似乎与“统治者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时代盛行的方式并无太大不同26。这种方式与信仰认同的本质相悖;我认为统治者在神学家的协助下就其人民的宗教进行谈判与不同教派的领袖进行谈判并无区别。另一方面,我并不否认天主教会曾就基督教合一问题进行过谈判,无论是1274年在里昂,还是1439年在菲奥伦斯,或是1561年在普瓦西,或是20世纪20年代在马林斯,这些谈判都是由一小群人进行的。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以教会权威为基础的天主教体系中,贝亚特(Baeiatite)在这些问题上的决定是可能的,但对于建立在私人判断原则为基础、否定等级制度观念的教派来说,这样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教派中,如果不事先征求整个团体的意见,就不可能达成一致。
认为可以通过务实的协商来调和对立的教义,这是世俗思想的特点,这不适合哲学家和信徒。
奥卢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希腊担任罗马总督期间所做的努力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形成了有趣而恰当的对比:盖利乌斯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或者说是一个今天被称为充满活力的人,他认为应该有可能一劳永逸地结束希腊哲学家之间的争论,因此他召集他们开会以达成一致意见:他想象自己能够在思想领域建立秩序,就像他试图在公共事务中恢复秩序一样。西塞罗温和地嘲笑了他的努力27。
盖利乌斯的集会有点像个笑话;但在几个世纪以来,也确实曾有过这种严肃的集会,并产生了真正的结果,这些会议涉及天主教徒和希腊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或某种类型的新教徒。此类联盟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在统治者的怂恿下在拿骚公国达成的联盟。这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联盟,每个教派都保留了自己的信仰,但所有教派都被组织成一个单一的教会体系。
不可否认的是,影响全体人民的宗教变革都是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的,或者是通过谈判实现的,甚至是专制法令要求来实现的;相关人员要么自愿地接受这些措施,要么被迫服从。这种做法的一个最近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在乌克兰东方天主教徒的遭遇;他们与罗马隔绝,并被苏联政府强行从属于莫斯科牧首教区。
虽然我们承认基督教合一的推动往往是出于部分政治原因,但我们不能忘记,人有两种,一种是管理事务的人,另一种是管理思想的人,而这两种事务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按照自己内在的逻辑来对待思想,只会导致空洞的口头协议而没有实质内容。
备注:
26. “谁的地区,谁的宗教”,即臣民必须信奉其统治者的宗教。这是 1555 年《奥格斯堡和约》通过的原则。[译者注]。
27. 西塞罗, De Legibus, 1, XX,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