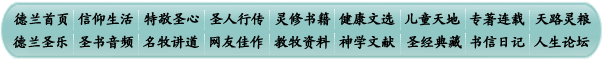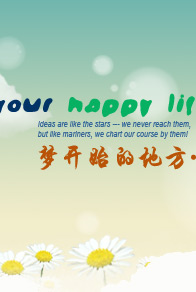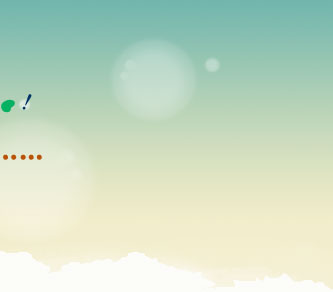目前,教会中普遍存在一种趋势,即将基督徒生命的目标从天堂转向人间,并将福音律法中“天主至上”的原则扭曲为“人类至上”。信仰的真理就这样被扭曲了,剥离了其中让世俗人反感的超性本质;正如主耶稣所说,“地上的盐”失去了它的味道(圣玛窦福音5:13)。面对这些颠倒黑白的教义18,信友们的反对意见软弱,抱怨也很无力,由此可以看出,目前主导天主子民普遍思想的错误有多深。这种教义冷淡主义(indifferentism)在当前情势下并不令人意外。历史上,无论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还是近代1945年的罗马尼亚天主教会、1947年的乌克兰天主教会或1957年的中国天主教会,在神职人员的带领下,整个民族都曾叛离过教会19。不可否认,人们对错误教义的愤怒逐渐消退,正是当前危机严重性的一个标志。
这种教义真理观念的丧失不仅仅是一种民间流行心态,如今在教会内的知识界从理论上为它辩护。举一个权威的例子,奥顿主教勒布尔乔亚(Mgr Le Bourgeois)写道:
“今天,我毫不隐瞒地表达我内心的喜悦,因为我看到我的教会,这个常被视为总是对自身过于自信、自认为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和裁判者’的教会,终于打破了这一形象,变得更加开放,开始理解、接纳他人的思想,承认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完成了一场‘真理行动’(opération vérité)——这与单纯地‘阐明和捍卫真理’完全不同。”。法国耶稣会期刊《Études》更是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新的原则:““今日已步入成年的信仰可以不再依赖教义;信仰已足够成熟,能够通过个人接触来发现天主。信仰不应建立在启示真理之上,而应通过历史事件的演变来加以理解。21”。
这一教义的现代主义起源及其内容是显而易见。信仰被说成已经“成长起来”,而实际上,真正的信仰却在萎缩和消失;一切都建立在被视为“体验天主”的感觉上;基督教被认为不是基于启示真理的历史事件,而是基于被转化为不断变化的知识范畴的人类经验;教会的中保地位被私人判断所取代,这正是路德运动和大多数现代哲学所依据的原则。
现代哲学的精神,早已被现代主义异端所接受,也导致天主教圣经诠释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在其官方机构——宗座圣经学院(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的正式表述中也有所体现。这种变化也导致了宗座圣经委员会(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变得无足轻重。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公开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点:新经古经之间关系的颠覆 (译注:梵二前公教术语,一直都是新经和古经。新约旧约二词出自新教,也是梵二后开始与新教同步的。建议依然沿用传统的新经古经)
古经中的言行不再被视为新经的预象,古经不再有先知性意义;恰恰相反,如今他们主张,新经只是根据古经内容所编造的故事。例如,古经记载的以色列选民中某些母亲的特殊怀胎和天神显现的历史事件,不再被视为《福音》中类似事件的征兆和预像。而现在,这些福音事件却被认为是信徒根据古代典籍的模式而虚构的情节。
此种观点,把《圣经》本质上向前推进的历史性事件进程逆转成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基于这个理论,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童年时期的记载,不再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被视为早期信友根据古经中的主题(如依撒意亚先知预言中的“童贞生子”)所拼凑的故事,用以表达他们不同阶段的宗教经验与信仰。
第二点:从历史到诗歌的转变
现今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新经仅仅是初期基督徒团体信仰的表达。这是一种新的教导,与教会自古以来的整个教义相悖。教会始终坚信,福音书并非宣扬信仰本身,而是宣扬人们信仰所依据的事实。在成为信仰的对象之前,基督的言行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世界中,正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它们就成为了信仰的内容;人们之所以能够相信,正是因为这些事件已经真实发生。
这种新奇的释经学与福音作者们的陈述直接矛盾。福音作者们从未声称他们是在宣讲他们所相信的东西,而是报道他们所听见和看见的,以便我们能够相信。让圣若望为所有福音作者发言:“我们将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传报给你们: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22”。(圣若望一书1:1)
这种新释经学的现代主义本质显而易见:基督信仰并非基于真的事实,而是基于经验;并非基于知识,而是基于感觉。(注:这种观点与教会传统训导背道而驰,因为教会始终教导,基督信仰的根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尤其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死亡与复活。这些事件并非信友们的主观经验或情感表达,而是天主在历史中的具体行动,为人类的救恩奠定了基础。)
第三点:将圣经与其他著作等同视之
现今有一种趋势,将圣经置于与其他著作相同的地位。根据这种观点,我们从圣经中寻求的并不是一系列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化状态及其神话的本质。基于此,整个梅瑟历史有时被贬低为神话;圣经的默感性也被解释为仅仅是对一系列无根据信仰的强烈民间信仰。同样,圣经中关于奇迹的记载也被否认,尤其否认基督的奇迹作为祂神圣使命的凭证价值,尽管多次大公会议已经把基督奇迹的性质定断为信理。23。
例如,甘廷枢机(Cardinal Gantin)曾说过:“我们蒙召信仰并非因基督行奇迹的能力;相反,正是我们对祂作为天主子的信仰,使我们能够相信祂的奇迹24”。这种说法令人惊讶,因为它公然违背了教会定断的信理。然而,类似言论如今屡见不鲜,其频繁程度已令人们大感麻木。
在思考教义统一性的丧失时,我们可以通过回顾大公会议时期关于教会教义统一的错误分析与预测,来提醒自己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迅速发展的程度。1962年四旬期的牧函中,米兰总主教蒙蒂尼枢机(Cardinal Montini,即后来的保禄六世)曾说:“今天在教会中没有错误、丑闻、偏差或滥用需要纠正”。当他成为教宗后,在1964年的首道通谕《祂的教会》(Ecclesiam Suam)中,他写道:“在现今时代,问题不再是清除教会中的某种特定异端或某些具体的混乱。感谢天主,教会中已没有这些”。然而,到了他任期的末期,保禄六世却发表了截然相反的声明,宣称“教会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25”。这种前后矛盾的言论不仅引发了关于心理问题的疑问,以及解释原则和天主安排处置世界的本质问题。
然而,我们在此关注的是教义统一性的丧失。如果说苏能斯枢机(Cardinal Suenens)的观点——即大公会议前在罗马被教导为确定真理的许多命题,在大公会议后被抛弃——并不完全准确,那么有一点却是真实的:过去在教义问题上的一致声音,如今已被众多不和谐的声音所取代。这种现象并非源于一系列细节上的分歧,而是信德本身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禄六世的话是正确的:并没有特定的错误需要谴责;需要谴责的是一种原则性的错误,因为这些具体的错误并非涉及基督信仰的次要方面,而是源于一种特定的,被圣庇护十世(St. Pius X)识别并谴责为现代主义的反原则。
备注:
18. 许多天主教徒对教义问题缺乏关注,以至于他们仍未意识到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译者注)
19. 在最后三个例子中,神职人员中并未出现明显的不正统现象。(译者注)
20. 《国际天主教新闻》(I.C.I)1983年第586期,第19页:“今天,我明确表示,我很高兴看到我的教会——她常常被视为永远自信、是一切真理的主宰与审判者——打破这一形象,以便开放自己,理解并接纳他人的思想,承认自身的局限,并最终开展一场‘寻找真理的行动’;这与解释和捍卫‘真理’是截然不同的。”
21. 瓦里隆神父(Father Varillon),在《研究》(Etudes)1977年10月刊中的《天主教信仰概要》(Abrégé de la foi catholique)中写道:“今天,成熟的信仰可以不需要教义:它足够强大,能够通过个人接触发现天主。信仰不应建立在启示的真理上,而应建立在历史中展开的事件上。”
22. 圣若望一书1:1:“我们将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传报给你们: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
23. 邓辛格(Denzinger),第1790和1813条。
24. 《罗马观察家报》(Osservatore Romano),1984年12月7日。
25. 特别参见第7-9、77和78段。
详细解释20 21:
这二段话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之后,教会内部一些人士对传统教义态度的转变。梵二会议后,教会内部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强调“开放”与“对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开放被理解为对传统教义的重新审视或淡化。
这种观点与教会传统训导相悖。教会始终教导,真理是来自天主的启示,而非人类探索的结果。教会的使命是守护并传授这一真理,而不是通过“寻找”来重新定义它。
这种倾向可能导致教义上的混乱,甚至背离信仰的核心内容。例如,若教会不再坚持其教导的权威性,信徒可能会对基本教义(如耶稣基督的神性、复活等)产生怀疑。
教会始终是天主启示的守护者,其使命是忠实地传授真理,而不是根据时代潮流重新定义真理。